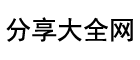东京审判简介
1946年1月19日至1948年11月12日,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战犯进行国际审判,这就是东京审判。
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根据莫斯科会议的规定发表了特别通告,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同时颁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其内容与英、美、苏、法4国在伦敦签署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基本相同。
由11国检察官组成的委员会于1946年4月29日向法庭提出起诉书,被告共28人,除3人已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外,实际受审25人。起诉书控告被告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
1948年11月12日,法庭宣布判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绞刑,木户幸一等16人无期徒刑,东乡茂德判处20年徒刑,重光葵被判处7年徒刑。7人判处绞刑,于1948年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
这次审判论定日军入侵并占领南京是事先预谋的罪恶,在日军占领南京后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30多万人。日军在占领南京期间对南京进行了强奸、抢劫、毁房屋等战争行为。这次审判确认侵略战争是国际法上的犯罪行为。
东京审判的结果
一、死刑
1、绞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武藤章等7人处以绞刑,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绞死在东京巢鸭监狱的死刑架上。
2、枪决:从1945年12月中旬起,中国也在一些地方设立了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从1945年底至1947年底,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35件,已判决的318件,不起诉的661件,经国防部核定判处死刑的110件(其中包括对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判处死刑、绑赴中华门执行枪决)。
3、自杀:一类是战败时自杀的,像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东部军管区司令官田中静一等。另一类自杀就是像杉山元等人,在被宣布为甲级战犯嫌疑人以后自杀,这种就纯粹是“畏罪”的逃避行为。
4、病死:东京审判被告最初是28人,但前外交大臣松冈洋右和前海军大将永野修身病死。
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16人处以无期徒刑(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星野直树、贺屋兴宣、木户幸一、小矶国昭、南次郎、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岛田繁太郎、白鸟敏夫、梅津美治郎、铃木贞一);对2人处以有期徒刑(东乡茂德20年,重光葵7年)。
除东京审判外,盟国还在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贡、伯力等地,对乙、丙级战犯进行了审判。据统计,被盟国起诉的日本各类战犯总数为5423人,被判刑者4226人,其中被判处死刑者941人。
三、“无罪”、被赦免
由于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出于利用日军力量进行反共内战的考虑,对侵华日军战争罪犯的审判竭力施加影响,中国军事法庭对很多战犯从轻从宽处理,甚至免于追究罪责。
制造“济南惨案”的主犯并在中国推行“三光政策”的日本方面军司令官和日本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于1949年1月被南京法庭宣判“无罪”而释放回国。
由于美国的对外政策转向反苏、反共、反对中国革命,急欲把日本变成反共的东方前哨阵地。因此,美国占领当局竟不顾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对日本战犯竭力庇护和大批释放。到1958年4月7日,所有未服满刑期的战犯都得到了赦免。
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同日,毛泽东发布命令,予以公布。
1956年6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对在抚顺和太原关押的335名(其中抚顺在押者295名)职务低、罪行轻、认罪表现较好的次要战犯免予起诉,立即释放。
1956年6月21日,第一批被免予起诉释放回国的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羁押的日本战犯共计295名; 1956年7月15日,第二批被免予起诉释放归国的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羁押的日本战犯共计296名; 1956年8月21日,第三批被免予起诉释放回国的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羁押的日本战犯共计306名。
1959年,我国政府又根据服刑战犯的悔罪表现,先后宽释了所有在押战犯。
四、“东山再起”
由于美国在战略政策上出现转变,盟军的总司令麦克阿瑟发出的所谓“战犯假释”的指令,岸信介等战犯因此被释放和减刑,之后又撤销了各种“褫夺公职”的法令,这些战犯和曾经被清洗的人再次担任了公职。
岸信介(Nobusuke Kishi) 1896年11月13日生,日本山口县人。前首相佐藤荣作胞兄。1936年后历任伪满政府实业部总务司司长、产业部次长和总务厅次长等职,被称为操纵伪满的五大头目之一。
1939年调回日本,历任阿部信行内阁、米内光政内阁、近卫文磨内阁等的商工省政务次官。
1942年4月在“大政翼赞会”支持下首次当选为众议员,同年10月任东条内阁商工大臣。
1943年任东条内阁国务大臣兼军需省次官。日本投降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关进监狱,1948年获释。
1952年解除“整肃”,同年组织“ 日本再建同盟”。
1953年当选为众议员,同年加入自由党。
1954年又与鸠山一郎等组成日本民主党,任干事长。
1955年自由民主党成立后,仍任干事长。
1956年任石桥内阁外务大臣。
1957年2月任首相。任首相期间,与美国签订新的日美安全条约。
在岸信介担任内阁首相的时候,他的内阁成员“由大臣到长官,曾经被清洗的人数达到了一半左右”。在回忆录中,岸信介得意地说:“自民党是我搞起来的,日本的命运只能由自民党来掌握。” 由他的话中就可以看出,日本右翼势力在日本是多么猖狂。
东京审判的意义
东京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法西斯同盟国,对在日本政府策划、准备、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中起过重要作用、担负主要责任的人物,进行的国际军事审判。
“国际社会采取法律手段对破坏人类文明的战犯进行审讯和制裁,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创举。”东京审判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性质的认定和对战犯战争责任的追究与判决,符合国际公约和国际法准则,符合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利益,符合人类对和平与正义的追求。
东京审判从法庭宪章的起草与公布、法庭的组成、对战犯的审判,直到认定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性质和对主要战争罪犯的惩治,都具有不可辩驳的法理依据。
东京审判在两年七个月的审理过程中,盟国并没有以战胜国的姿态对战争罪犯以主观、武断的判决,而是以国际法为根据,在大量的人证、物证的基础上,在给予战犯以充分的自我辩论的基础上而作出的法律判决。“这一点已经得到世界的公认。”
东京审判不仅从法律的角度认定了日本发动的对中国、东南亚和美英等国战争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而且通过审判日本主要战犯,公开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暴行,尤其是侵华14年间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宋志勇介绍,在法庭上,战时日本曾严密封锁的“南京大屠杀”等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被揭露,为审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从政治角度看,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一样,对于制止侵略战争、保护正义力量、倡导世界和平、促使用战争以外的方式解决争端等起到了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东京审判向全世界宣告,策划、发动侵略战争是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参与战争犯罪的人,要对侵略战争负责。
东京审判是一场严肃、正义的审判,它惩罚了战争罪犯,维护了国际法的尊严,为人类和平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东京审判的影响从未离开,却被遗忘多年
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25岁的高文彬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参与了东京审判的全过程。他是目前中国唯一健在的,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亲历者。
文 | 陈之琰
网络编辑 | 周晓曼 林小雨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们,前排右二为中国法官梅汝璈,后排左一为印度法官帕尔。东京审判中,帕尔是唯一主张日本甲级战犯全员无罪的法官。
2016年4月28日上午,95岁的高文彬早早地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70周年学术论坛。5月3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审判开庭70周年纪念日。
穿着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乱,高文彬一个人坐在会场外,不断有人走过来与他握手、合影、交谈。媒体记者围着他,都在请他讲70年前的那段特别经历。
“每天开庭前一天下午,日本人就在门口排队,几百米长,就为了张票子。他们认为东条英机这些人是国家英雄,成了战犯,他们觉得很糊涂。所以,国际法庭开庭他们就来看。日本人不了解,他们的军人竟像野兽一样。”
彼时,高文彬刚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一年未满,成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处翻译官、中国检察组秘书。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25岁的高文彬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参与了东京审判的全过程。他是目前中国唯一健在的、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亲历者。
这一次,老人走到公众面前,与其他东京审判的亲历者及亲历者后人一道发出倡议:在上海建立东京审判暨战后对日审判纪念馆。
帕尔的照片最大
“建立东京审判纪念馆,将以史实对右翼翻案风予以有力回击。有鉴于此,我们郑重倡议建立东京审判暨战后对日审判纪念馆!”东京审判亲历者及后人的代表向隆万如此倡议。
在2006年上映的电影《东京审判》中,演员曾江饰演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濬是向隆万的父亲。除了向隆万和高文彬之外,署名倡议人还有:当年的中国检察官翻译张培基、中国法官梅汝璈的女儿梅小侃、儿子梅小璈和中国检察组首席顾问倪征之女倪乃先。
国际法庭开庭,日本人争相前去观看。东条英机这些人原来是国家英雄,现在成了战犯,他们很困惑。图为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日军甲级战犯被告者列队出庭。(CFP/图)
倡议者们说,选择上海,是因为70年前,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团在此地组团。17名团员中,法官梅汝璈是当时复旦大学的教授,检察官向哲濬是上海第一特区地方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同行的年轻人中,有十余名来自上海的大学,像高文彬一样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就有10位。
“倡议建立东京审判纪念馆,其实是日本人‘教育’我们的。”向隆万说,“我去过靖国神社的‘游就馆’(相当于战争博物馆),那里关于二战的内容满是对中国的歪曲与污蔑,称‘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事件都是由中国挑起。现场就有很多的日本青少年。这对我们是很大的触动。”
宣读倡议书之前,向隆万向在场的所有人播放了一段摄于东京审判原址的视频——
“指导战争并不是犯罪。如果指导战争是犯罪的话,那么麦克阿瑟、杜鲁门、毛泽东、金日成,都应该带到这个法庭来受审。”一位操日语的讲解员这样说着。他向参观者推荐印度法官拉达·彼诺德·帕尔的观点。帕尔是东京审判中唯一主张日本甲级战犯全员无罪的法官,并为此提交了长达1275页的判决意见书。
帕尔的主要论点包括“既然承认战争,杀人行为就是必然行为”“突袭珍珠港是美国向日本发出通牒后,日本出于自卫而诉诸武力”“东京审判是美国进行复仇的审判”,以及“东京审判是战胜国审判战败国”。
东京审判原址目前位于日本防务省内,与70年前相比,梅汝璈坐过的法官席不见了,原来的被告席则成了日本旧军服的展示区。在所有的展柜里,帕尔的照片最大,资料也最多。
“日本对公众进行历史教育的形式很平和。讲解员们经常是笑着,不会慷慨激昂地谈仇恨。但错误的历史知识就这么看似理性地、潜移默化地传输给了下一代。”历史题材画家李斌为了创作新作《东京审判》,到日本搜集材料并拍摄下了这段视频。
李斌绘制的《东京审判》草图局部,该作品将于2018年11月12日,即东京审判闭庭70周年纪念日正式问世。
李斌说:“以往,我们围绕着抗日战争历史的纪念馆总给人以悲壮的、哭诉的、仇恨的感觉。但这段历史中的东京审判却如此不同。所以,我们希望能建立一个苦难之外,既有胜利者姿态,又具有法理背景的纪念馆。”
向隆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之所以在历史过去那么多年之后才倡议建立东京审判纪念馆,是因为不仅对于公众,即便在学界,东京审判也一直是一场“被遗忘的重要审判”。
“研究东京审判最多的是日本人”
学术论坛现场,除了发布建设纪念馆的倡议,还同时举行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国部分》(12卷)的首发仪式。时隔70年,东京审判中有关中国部分的庭审内容,终于以中文形式,出现在公众面前。
东京审判整个过程长达31个月,开庭818次,控辩双方提供证人1194人,其中419人出庭作证,检方与辩方共提出证据4336件;庭审记录48000页,判决书1200页。
东京审判现场。
涉华庭审记录中文版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这两家出版社曾于2013年6月、2014年3月和2015年9月分别出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英文版》(全80卷)、《远东国际法庭证据文献集成·日文版》(全50卷)以及《国际检察局询问记录·英文版》(全70卷)。这些外文档案文献原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日本国士馆大学等地。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对东京审判研究的关注度一直很低。”向隆万分析,由于东京审判结束后很快爆发冷战,美国和日本从对立成了盟友,多少淡化了东京审判,而日本国内否定东京审判的思潮开始兴起。此外,参与审判国中不少国家都有殖民历史,加上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放的两颗原子弹,都使西方国家在东京审判的正义性问题上多少有些“气短”。
另一方面,1949年国内政权更迭,东京审判中国代表团由国民政府派遣,回国后大多数成员又留在了大陆。不论在台湾海峡的哪一边,这群人都显得处境尴尬。
于是,那场大审判的亲历者成了国内的“边缘人”,而对那段历史的研究也一同被世人忽略了。法国律师艾迪安·若代尔生前的一部著作直接称东京审判为“被忘却的纽伦堡”(记者注:1945年11月21日至1946年10月1日间,在德国纽伦堡举行的对欧洲轴心国领袖进行的数十次军事审判)。
在全球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投入最多的是日本学者。
“日本对东京审判的各种议论从未间断,对东京审判的研究和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更已相当广泛、深入。东京审判在中国受到瞩目仅仅始自近年,还是拜影视之赐,研究层面还远远落于人后。”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说。
“日本对东京审判的研究一直是全世界数量最大的,除了极右立场的研究,也有不少从学术角度聚焦东京审判的细节和档案,在法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领域都有建树。”青年学者龚志伟说,“很多档案日本也没有,不少日本学者就自费找档案、做研究。”
1983年,日本在原巢鸭监狱旧址建造的太阳城召开了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次东京审判国际讨论会,中国只有一位正巧在东京的访问学者列席。龚志伟说,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对东京审判的研究大多是泛泛之论。
在向隆万印象中,转变发生在二战胜利60周年之时。2005年9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评价东京审判“使发动侵略战争、双手沾满各国人民鲜血的罪魁祸首受到应有的惩处,伸张了国际正义,维护了人类尊严,代表了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共同心愿”。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在正式讲话中谈到东京审判。
由于亲历者后代的特殊身份,向隆万是国内最早的东京审判研究者之一。理工科背景的他并不是历史学者,只是在2002年退休之后,才有机会与夫人一起到美国找到了有关父亲和那场审判的一手资料。
2006年,向隆万赴美翻拍了近百张照片,查阅复印了一百多页父亲的讲话。为了节约开支,他和妻子住在新泽西州一个朋友家,每天清晨,朋友的太太开车送他们到火车站。他们乘火车到纽约,而后转乘地铁至位于曼哈顿的哥伦比亚大学,晚上再原路返回。
2010年,向隆万根据搜集到的资料编写出版《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一书,收录了父亲在法庭上10次讲话的英文原稿、中文翻译,并附有母亲周芳回忆录。该书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关注,2011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65周年纪念日,全世界唯一专事东京审判研究的学术机构——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东京审判研究中心”)诞生。
高文彬是全程参与东京审判、唯一健在的中国亲历者,已95岁高龄。(CFP/图)
只要日本想成为“正常国家”
“庭审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和被告语言日语,所以留下的档案文献都以这两种语言为主,也为中国的研究者和公众带来了理解那段历史的难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此次发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国部分》经过了约四年的工作,是该中心的最新研究成果。
作为中文版涉华庭审记录编译的统筹者和审校者之一,龚志伟从2012年11月起就投入到联系译者、编译和审校的工作中。
“四年多的时间里,最大的困难是英、日文版的出入,因为有些内容不对被告翻译,从而增加了校对的工作量。”龚志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除了这些,还有中日人名、地名与英文的转换。东京审判的庭审资料相当详细,人名精确到某一个中下层日本军官,地名具体到一个村庄,这些都需要不断从史料中寻找准确的信息。”
还是博士生的龚志伟,原本学的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是两汉时期。2011年研究中心刚成立时,他成为其中一员,并自愿将研究重心改为东京审判。谈起原因,龚志伟称东京审判是中国史中难得的“研究者少、意义又重大”的研究领域。
“虽然我们叫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但从成立至今的五年里,中心的研究者花了大量精力在做档案、资料整理的工作。自2013年起,连续三年我们都出版了数十卷体量的档案资料集,并制作了精密详细的索引,但这些都还只是东京审判保留下来文献中的一小部分,所以给学者们留下了非常多的研究余地。”龚志伟说。
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合照。
程兆奇说,除东京审判本身,战后亚洲的美、中、英、法、荷、澳、菲设立的一个准A级和四十九个BC级法庭的审判以及苏联、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日审判,与东京审判同为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这些审判共同成为战后东亚审判的有机组成。此外,如中国地方法院的“汉奸”审判,作为战后涉日审判,也可纳入以“东京审判”为标志的战后对日审判的范围,成为研究者的研究对象。
对这些东京审判研究者来说,研究这场审判还不仅是对历史的洞察。在诡谲的国际政治中,东京审判具有与其他历史事件不同的现实意义。
由于长年收集国外有关东京审判的著作,向隆万发现,在日本近年出版的著作中,常常以“为什么要研究东京审判”作为开场白。但这些论著大多不是指审判本身的“学科”意义,而是指东京审判派生出来对现实仍起着重要影响的“历史意义”。
2006年,日本出版学者北冈俊明的《东京审判是捏造》一书,称研究东京审判就是为了否定东京审判。该书第一节“为什么今天要研究东京审判”有两个小标题,一是“日本人自信心丧失的根本原因是东京审判的精神创伤”,二是“否定东京审判是日本一切政策中最优先的政策”。日本以东京审判为主题的著作中,约有半数的观点如同此书。
“即便是日本左翼学者,关注点往往也不在东京审判本身,也往往离不开东京审判争持的现实意义。例如,山田朗所著《东京审判》的副标题写道:东京审判是‘历史认识问题的原点’。研究和处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中日关系,绕不开东京审判这块基石。”向隆万说。
龚志伟认为:“东京审判是在司法层面上对日本二战罪行的一次大总结、大清算,其影响延续至今。日本始终觉得东京审判是压在国家身上的一个封印。如果日本要成为安倍口中的‘正常国家’,废除《宪法》第九条——放弃发动战争、不保持战争力量及否认国家交战权,就必须先否定东京审判。”
在东京审判后不久,日本右翼就翻译出版帕尔法官的《异议书》,宣传唯一反对日本甲级战犯有罪的观点,在靖国神社等地建立多处帕尔纪念碑。2015年,自民党政调会长稻田朋美称计划在党内设立新组织“验证”东京审判,被普遍解读为企图否定东京审判。
“因为这场审判是对日本在二战行为的盖棺论定。东京审判和南京大屠杀、珍珠港事件、进攻苏联和东南亚等历史事件不同。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射线。东京审判通向现在,通向未来。虽然审判在1948年11月就结束了,但它的影响从未离开。”龚志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