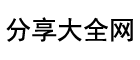安德烈·奇卡提罗(Andrei Chikatilo) 勃起障碍的罗斯托屠夫
安德列·奇卡缇洛(Andrei Chikatilo),有着[俄罗斯食人魔]之称的魔鬼,二十世纪最骇人听闻的罪犯之一。
他在一九九零年被捕入狱,称述自己杀人及肢解尸体的方式如下:
先用短刀肆意刺杀被害者,等到对方奄奄一息,再一刀毙命。接着,把尸体肢解成几大块,再陆续分为小块。他曾大口咬下尸体的舌头吞下肚内,再将尸首分家,掏空内脏后,如果是少年,就切断阴茎,如果是少女,就切下小阴唇;之后再切下要食用的肉。
后来他在法庭上表示,咬断牺牲者的舌头吞下肚的刹那,是最美妙的时刻。
奇卡缇洛5岁时被灌输了他哥哥的失踪是被“饥饿与绝望的邻居”绑架并吃掉了这一观念,很可能是他后来产生食人心理最初的诱因----他认识到即便是人类,同类也是可以相食的.形成了他扭曲的人生观与价值取向。 奇卡缇洛在幼时亲眼目睹母亲被德国士兵轮奸,这直接造成了他成年后难以启齿的功能性勃起障碍,使他很难进行正常的性行为.奇卡缇洛的父亲被诬蔑为叛徒,社会对其家庭的抛弃与歧视促成了他报复社会的心理(强烈的反社会人格障碍);通过猥亵年轻妇女及男童并将他们杀死后奸尸以获得性满足。
奇卡缇洛往往将被害人骗至森林等人迹稀少的隐秘所在(借口通常是请他们驾驶并不存在的汽车,或者参观并不存在的房屋),将被害人扼死或用刀反复戳刺腹部致死(被害的妇女与儿童对身高一米九三的奇卡缇洛几乎不可能实施任何有效的反抗),然后进行奸尸、虐尸,并剖取尸体的器官食用,他甚至声称“最喜欢”饮用被害人的鲜血。奇卡缇洛每次行凶都有一个残忍的共同点就是将被害人的眼球取出。奇卡缇洛案的审判法官莱昂尼德·阿库布扎诺夫(Leonid Akubzhanov)在判决书中对他的暴行叙述为: “他(奇卡缇洛)咬下被害人的舌头,割下他们的性器官,打开他们的腹腔,最后将他们折磨致死”。由于其一贯将被害人开膛破肚的残暴手段,奇卡缇洛被冠以“开膛手”的绰号;又因为他经常将被害人诱骗至森林地带杀害并掩埋尸体,也被BBC等媒体称为“森林地带杀手”。
1978年12月22日,奇卡缇洛用一块美国产的口香糖将年仅9岁的女孩叶蕾娜·扎科特诺娃(Yelena Zakotnova)诱骗至其位于格鲁舍夫卡河(Grushevka River)边的小屋内。奇卡缇洛进屋以后立刻露出了他邪恶的脸孔,他将扎科特诺娃扑倒在地,堵住了她的嘴并蒙住了她的眼睛;随后奇卡缇洛强奸了她多次,并在发泄兽欲的过程中发现扎科特诺娃痛苦的喘息更能激发他的性欲。奇卡缇洛松开扎科特诺娃被束缚的身体后,这名年幼的女童当时就对他说要出去报警,奇卡缇洛闻后立刻在她的腹部猛戳三刀并将她投入河中。扎科特诺娃的尸体被发现后经法医检查确定死因为“溺水及失血性衰竭”----这个可怜的孩子被丢进格鲁舍夫卡河的时候还活着。
一名叫斯维塔娜·格伦科娃(Svetana Gurenkova)的女孩告诉警方她最后看到扎科特诺娃的时候,被害人和一名又高又瘦、身着黑色外套的戴眼睛中年男子在一起。警方根据格伦科娃的目击描述制作了犯罪嫌疑人的画像,与画像中的嫌疑人身高体貌“十分相似”的奇卡缇洛(其实就是他)也受到了警方的调查讯问,奇卡缇洛河边小屋门口的血迹更加重了他的犯罪嫌疑,但他居然用一番辩白最终使自己安然脱离了警方的怀疑范围(相信奇卡缇洛比画像中的嫌疑人年轻太多且平日从不戴眼镜是警方排除他作案嫌疑的主要原因,但也有人怀疑他是通过贿赂手段脱身的)。这次“冒失”的初犯使奇卡缇洛老实了三年多的时间,为了分散并压抑自己的冲动,1981年的时候,他甚至在罗斯托夫的一家工厂找了份采购工作,并打算过一种“平静、安分守己的生活”,而事实上,他的“打算”仅持续了6个月而已。
奇卡缇洛的第二名侵害对象是拉瑞萨·卡臣科(Larisa Tkachenko),相比较第一名被害人而言,这个17岁的女孩则是出了名的行为不检点----卡臣科是个喜欢用身体来交换美食醇酒的放荡尤物。奇卡缇洛很轻易就将她骗至一处偏僻的丛林里并将她扼杀后奸尸;在事后奇卡缇洛围绕着尸体“欢快起舞”----他彻底爱上了这种籍由杀戮获得的性快感。
1982年6月,奇卡缇洛在出差采购的途中奸杀了13岁的少女琉芭·伯约克(Lyuba Biryuk);12月,他又以同样的手法谋杀了15岁的劳拉·萨基珊(Laura Sarkisyan),案发后经查证,他在上述两起案件之间的六个月内还杀害了至少5个人----其中包括两名男童。1983年夏天,奇卡缇洛再度制造了三起谋杀,其中年龄最小的是年仅7岁的男孩艾格·古德科夫(Igor Gudkov)。很显然,奇卡缇洛已经更多地把“兴趣”转向了男童,他甚至偶尔也会在街上寻找被害人----主要针对离家出走的儿童和站街揽客的妓女。
虽然奇卡缇洛有妻子和一双儿女,但是不能进行正常的性生活依旧令他感到无比烦躁。他在学校担任宿舍管理员期间就时常利用职务之便猥亵男学生并强迫他们为他咬,当校方和学生家长发现后奇卡缇洛遭到了一顿暴打并且丢掉了工作;“万幸”的是由于顾及学生与学校的颜面,他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奇卡缇洛并不是同性恋者,只是长期的性压抑促使他通过其他非正常的方式(比如猥亵男童)寻求发泄;在他某杀了第一个侵害目标并从中获得了充实的性快感后,奇卡缇洛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寻找“性福”之旅。奇卡缇洛案的调查员阿米尔克汗·雅迪耶夫(Amirkhan Yandiyev)说:“他的目的是性行为”。该案的检察官对奇卡缇洛的评价则是:“他对被害人没有任何的悔恨,他所同情的只有他自己”。更有传言说一个日本人欲出资百万购买奇卡缇洛的头颅用以研究这个拥有明确性动机的变态连环杀手。
奇卡缇洛归案后一直辩解说对自己的暴行无法控制,并试图以自己有精神分裂的倾向来逃避或部分逃避法律的制裁。他称自己在生活里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并且是一个“模范丈夫”,只是在某种特定情形下才会成为一个屠夫:“我发现自己在不同的环境中会变成另一个自我,我无法控制,(这些谋杀)就像是被魔鬼控制了一样,尽管它违背我的本性,但是我无法抗拒”。奇卡缇洛几乎每次行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被害人的眼球取出,他认为被害人的眼睛会保留他的信息,但也许他更害怕的是被害人那死不瞑目的眼神。
奇卡缇洛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一个魔鬼,历史原因以及苏联当时的国家政策对他造成的影响尽管是间接的,但无疑是巨大的。在奇卡缇洛出生前后,整个国家在斯大林集体化政策(Collectivization)的调控下,爆发了大范围的饥荒。即便是他的家乡,在当时被誉为“苏联粮仓”的乌克兰,也是哀鸿遍野,饥饿吞噬掉了数以百万计的家庭;他的哥哥斯特凡(Stefan)就是在1931年失踪的。奇卡缇洛的父母认为年幼的斯特凡很可能被邻居吃掉了(这在当时属于很正常的“意外”)----奇卡缇洛从懂事开始就被不停地灌输这一观念。中年丧子的悲痛既值得同情,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奇卡缇洛夫妇恐怕忽略了他们第二个儿子安德列·奇卡缇洛是否也能正确理解他们的感受。自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国家进入了风雨飘摇的混乱时期,奇卡缇洛5岁时目睹了母亲被入侵苏联的德国士兵轮奸,这很可能是导致他成年以后出现性功能障碍并很难进行正常的性生活(虽然多年以后他的妻子给他生育了两个孩子,但是长期的性压抑仍旧使他开始盲目寻找发泄的途径)。他的父亲在德国入侵苏联期间被逮捕并关押在集中营里,最后凭借坚强的毅力得以生还。而在那个年代荒谬的政治背景下:一旦被敌人逮捕,牺牲了是“民族英雄”,活下来就一定是“背判了革命”----他的父亲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为了红色苏维埃政权的叛徒。由于有一个“判国通敌”的父亲,奇卡缇洛的家庭被当时整个苏联社会所唾弃;有证据表明他曾经是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但是由于家庭的政治问题无法进入理想的学府继续深造,最后只是在一所学校担任宿舍管理员,这可能也算一种“下放劳动”,“向工人阶级学习、靠拢”吧。众所周知苏联当时在斯大林的铁腕统治之下冤案无数,奇卡缇洛家庭的遭遇也许并不是最悲惨的,但是奇卡缇洛由此逐渐形成的反社会人格却在随后而来的和平年代中以一种最为疯狂的方式爆发了。
苏联一直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存在连环杀手,媒体也一直宣称连环杀手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衍生物,具有高度先进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产生这样的野兽。后来美国曾经拍过一个电影Citizen X讲述这起案件,其中深刻描写了有良知的警察为了追查凶手遭到苏联政法体系中各级官僚的长期压制和掣肘。苏联政府这种对连环杀手一相情愿的否认态度也因为这个案件而得名,被称为“Chikatilo综合症”,用来指代由于政治,宗教,文化传统等主观因素而对连环杀手现象的盲目否认。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集体自我欺骗对案件的侦破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当时新闻媒体也处在封锁制度下,致使人们对社会上潜伏着这样一个恶魔一无所知,从而缺乏应有的警惕性;当时苏联的种种制度上的弊端造成了奇卡缇洛能够疯狂作案12年之久,尽管他最终被裁判要对约53起谋杀案负责,但许多学者认为奇卡缇洛大概共犯下了70宗命案。
另外,奇卡缇洛本身血液的特性也是造成他屡次脱离侦查人员怀疑的重要原因----他的血型是AB,但B抗原体有时很不明显甚至显示不出来。案件调查人员曾多次将他的血样与被害人身上调取的精液或血迹样本进行比对,但是结果往往发现二者并不是同一血型;这在客观上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1994年2月15日,安德烈·罗曼诺维奇·奇卡缇洛在狱中被执行死刑,在行刑用的那把手枪打穿他后脑之前,他双目空洞地喃喃自语道:“我是自然界的一个错误,一头疯狂的野兽------”
奇卡缇洛,你不是一个自然界的错误,你和那数十条无辜的生命一样,都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