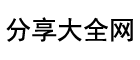以下文字资料是由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后发布的内容,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分类:社会民生 >>...问题描述:
谁能帮我找一下美国作家凯鲁克写的<在路上>那本书的有关信息,越多越好,谢谢了!
解析:
豆瓣网的简介douban/subject/1051440/
旌旗网的最便宜,16元,book.jingqi/63325
许多不畅销的书是不能在网络全部阅读的,微星网络图书馆有但需要付费。
评《在路上》 / 〔美〕吉尔伯特·米尔斯坦xishu/channel/main/contentdetailx?GUID={17A96F94-94E9-4DD4-96DF-9443D4E815DA}
漫长的喜悦之路 / 戴维·德普西xishu/channel/main/contentdetailx?GUID={182B726C-B8F4-4B32-B50B-E919C115D8CC}
“垮掉的一代”、凯鲁亚克和《在路上》 / 文楚安
xishu/channel/main/contentdetailx?GUID={FD6C1CEA-AE2E-4C9D-99B0-C65CDCCEE9F3}
我旅游生活中堪称最伟大的一次经历即将开始。一辆后部拖有平板挂车的货车上,躺着约摸六七个小伙子,坐在驾驶位上的是两个明尼苏达州的年轻农夫,都长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他们总是乐意把在路上看见的人都搭上车——笑呵呵的,很开心。这两个乡下佬长得挺英俊,是你在旅途中最巴望见到的那种人,都身穿棉布衬衫和工装裤,再没别的什么;手脚都很粗大;坦率热情,对于在路上遇到的任何人或看到的任何事总是满面笑容,就好像在打招呼似的。我跑上前去问道:“有空位吗?”他们说:“有,快上车,上车的人都有座。” 还不等我在车厢里坐好,货车便开了。我的身子摇晃着,一个乘客扶着我,我趁机坐下。有人递给我一瓶劣质威士忌酒,就只剩瓶底那么一丁点儿。内布拉斯加的天空中细雨 ,一直不停地下着,然而别有一番诗意,我猛地将酒喝完。“啊哈,咱们又上路了!”一个头戴棒球帽的小伙子叫起来,他们加快车速,每小时七十英里,公路上的行人从车旁一闪而过。“打德海因出发就一直这样,他妈的快得发疯,从没停过。要撒尿你得一个劲儿嚷,要不你就只有撒到空气中了,伙计,得憋住劲,是的,得憋着劲儿!”
我瞧了瞧车上的同伴,两位从北达科他州来的农场小伙子头戴红色棒球帽。一看这种帽子就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来。眼下正是收获时节,他们得赶回农场干活;父母让他们夏天外出,在路上到处逛逛。还有两位城市小伙子来自俄亥俄州哥伦布城,都是中学橄榄球队员,嘴里嚼着口香糖,不停地眨着眼,顶着细雨哼着歌,他们说这个夏天要搭车走遍美国。“我们现在去洛杉矾。”他们大声对我说。
“去干吗?”
“干吗?我们也说不准,这不用操心。”
车上还有一位小伙子,又高又瘦,他那神情我看起来很不顺眼。“你从哪儿来?”我问道。我正好坐在他旁边,平板车厢老是颠簸不止,想坐得稳稳的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没有车栏。这家伙慢慢向我这边靠,张开嘴说:“蒙——大——拿。”
最后我得提到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基恩和他的同伴。基恩这小子个儿不高,皮肤黑黑的,搭乘货车跑遍了美国。他到处流浪,虽已三十岁,可模样儿看起来挺年轻,让你根本无法猜出他的实际年龄。他盘着腿坐着,在数百英里的行程中,一直望着田野,一声不吭,最后才侧过头来对我说:“你到哪儿?”
我回答我去丹佛。
“我有个姐姐住在丹佛,可我好几年没见到她了。”他的声音慢腾腾的,听起来很悦耳,看得出来,脾气挺和善的。他的同伴一头金发,个儿高高可只有十六岁,也是一身流浪汉的装束;我这是说,铁路煤烟,货车车厢里的尘土,还有常常在地上过夜,他的衣服己被折腾得又旧又破,黑乎乎的了。那金发少年也沉默寡言,好像是因为什么事才离家出走似的,这种事儿可以说十有八九千真万确,只需从他老是盯着前方、嘴唇湿湿的、焦虑不安地想着心事的神情就看得出来。从蒙大拿来的那位瘦高个儿偶尔对他们说上几句话,语气尖酸刻薄,而且那笑容也明显不怀好意。他们没理会他,瘦高个的这种盛气凌人并未收敛,每当他张牙露齿直对着你的脸似真似假地傻笑时,我就格外讨厌。 “身上带钱了吗?”他对我说。
“不算多,到丹佛前也许够我买一小瓶威士忌。你呢?”
“我想总会有地方能挣到一些钱的。”
“什么地方?”
“任何地方都可以。你总可以引人上钧,投其所好,不是吗?”
“是这么回事,我想你可以这么干。”
“除非真缺钱,我不会犯傻那么干。我这就赶去看我父亲,我得在夏延下车,再转道,这些发疯的小伙子要去洛杉矾。”
“直接开往洛杉矾吗?”
“是的,如果你打算去洛杉矾,就搭这车去。”
我寻思片刻,这车一整夜将经过内布拉斯加州、怀俄明州,上午穿过犹他沙漠,大概在下午可以进入内华达沙漠;确实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到达洛杉矾,我原来的计划似乎就得改变了。可我得到丹佛,我也得在夏延下车,再往南搭车九十英里就可到目的地。
两位明尼苏达农场小伙子开着的这辆车终于在北普拉特市停下吃饭,我很高兴;我想见他们。两人下了车,微笑着对我们打招呼。其中一个大声说:“下车撒尿!”另一个说:“该吃饭了。”不过,我们这些人中只有他们有钱去买吃的。我们没精打采,慢慢跟着他们进入一个像是由几个女人合开的饭店坐下,打量着四周桌上的汉堡包和咖啡;这时他们大口大口地把一大堆食品吃个精光,好像是回到了自家母亲的厨房里似的。
这两人是兄弟,此行到洛杉矾是要把农场的机器运回明尼苏达,能赚上一大笔钱。因此,到西海岸一路空车,顺便也把路上的每一个搭车者载上,如此往返己是第五次了。一路上他们开心极了,对任何事都有兴趣,脸上总是笑呵呵的。我试图同他们聊上几句——对我来说,那情形简直就像是一个笨蛋去讨好船长似的,倘若我把这辆车看做一艘轮船的话——我所得到的回报只是两张笑意灿烂的面孔还有满口白净净的好牙。
车上的人除了那一对流浪汉基恩和金发少年,都同他们一道来到饭店。我们返回时,基恩和金发少年仍呆在车上,神色沮丧。此时天黑了。趁两位司机吸烟的当儿,我跳下车想去买一瓶威士忌,为的是好在寒气逼人的夜晚热乎身子。我把这想法对他们讲,他们笑着说:“快去,快些!”
“你们也来喝上一杯!”我对他们说,劝他们也下车。
“啊,谢谢,我们从不喝酒,快去吧!”
蒙大拿瘦高个和两个中学生小伙子同我一道在北普拉特市的街道上逛,终于找到了一家威士忌酒店。他们,包括瘦高个,都凑了几个钱,买了一瓶五分之一加仑的威士忌酒。若干高大而脸色阴沉的男人望着我们从带有临时门廊的建筑旁走过,街道两旁是一排排像正方形盒子一般的房屋。这些看起来萧索悲凉的街道之外是一派平原景色。在北普拉特市的空气中,我感觉到有某种异样的东西,可我又说不出这种感觉从何而来,至少在五分钟内我是这么想的。我们回到车上,继续上路。夜色很快来临,我们都喝了一日酒。突然间,当我向外凝视,普拉特郊外碧绿的田野正从视野中消失。令我万分惊异的是在你所无法目及的远方出现了一片狭长而平坦的荒原,除了沙砾和灌木丛一无所见。
“这是什么鬼地方!”我大声对瘦高个嚷道。
“小伙子,咱们开始看到大牧场了,再给我喝一杯。”
“啊呀!”那两位中学生一齐吼叫起来,“怪长的!要是当初哥伦布同他的那帮人到了这儿,他们会怎么惊奇,瞧,瞧!”
司机向着正前方开车,坐在驾驶座上的弟弟尽量减低车速,公路此时也起伏不平,中间部分凸起,路面松软;公路两侧各有四英尺深的水沟;卡车弹跳起来,从路的一边歪向另一边——幸好当时迎面没有别的车开过来——不然,我猜想我们准会连人带车翻个斤斗四脚朝天了。不过,多亏司机兄弟俩驾驶手艺高超。内布拉斯加行程中最难走的这部分——还有科罗拉多州处处可见的类似险路,总算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我明白,我们终于越过了科罗拉多州,虽然我没公开对任何人说,然而顺着西南方向望去,到丹佛不过只有百多英里罢了。我高兴极了,不禁高呼起来,我们相互传递着酒瓶。这时,夜空中星星闪烁,从卡车两旁往后迅速退去的沙丘越来越模糊了,我觉得自己像一支箭正在向前疾飞。
突然,密西西比的那位基恩终于从他久久的沉思中醒过来,双脚不再盘在一块儿,向我侧过头来,张开嘴又向我靠近说:“看见平原就让我想到得克萨斯。”
“你是得克萨斯人?”
“不,先生,我从莫兹西比的格林韦尔来。”他说到这个地方时就这么发音。
“那小子是哪儿人?”
“他在密西西比碰上点麻烦,是我帮他逃离了那儿。这孩子从没单独离开过家。他毕竟还是孩子,我得尽力照料他。”基思虽说是白人,可就聪明及不屈不挠而言,他有点儿像一个老黑人,甚至颇像纽约的那位嗜毒成癖的埃尔默·哈斯尔;不过,他是一个在铁路上奔波的哈斯尔,一个浪迹天涯的传奇性人物哈斯尔,每年都要一次又一次地周游全国;冬天到南方,夏天到北方,仅仅因为在他所停留的地方一呆久了,就总会使他厌倦。也因为他无处可去,四海为家,总是不停地在星空下,主要是在西部的星空下流浪。
“我去过好几次奥格登。要是你去那儿,我有几位朋友,咱们可以得到帮助。”
“我要从夏延赶到丹佛去。”
“真见鬼,那就得一直往前,不必每天搭车。”
这主意倒挺不错,可奥格登是个什么地方?于是我脱口而出:“干吗非要到奥格登?”
“许多小伙子都打那儿经过、聚会,你在那儿什么人都能结识。”
多年以前,我曾同一个又高又瘦的伙伴去过海上。他是路易斯安那州人,绰号叫做瘦大个哈泽德,真名叫威廉·霍尔摩斯·哈泽德。他自己心甘情愿当流浪汉。小时候,他曾看见一个流浪汉求他母亲给一块馅饼吃,他母亲那样做了,等那流浪汉上路后,哈泽德对母亲说:“妈妈,那是什么人?”“干吗问这个?一个流浪汉。”“妈妈,我长大要当流浪汉。”“住嘴,那可不是哈泽德家的孩子要干的事。”尽管如此,那一天的情景他可永远没忘记。长大后,他在圣路易安那大学打过一阵橄榄球,后来果然成了流浪汉。瘦大个和我夜晚常常在一起边讲故事边吸放在纸制容器里的烟叶汁。眼下这位密西西比的基恩的行为举止,令我不得不回想到瘦大个哈泽德,两人确实有某些相似之处。我于是问道:“你在什么地方知道一个叫做瘦大个哈泽德的人?”
他回答:“你可是说那个总爱大笑的高个儿家伙?”
“唔,好像是他。他是路易斯安那州拉斯顿人。”
“没错,有时人们称他路易斯安那瘦大个。是的,先生,我确实见到过瘦大个。”
“他可是一向在东得克萨斯油田干活?”
“是的,可他眼下在放牛。”
看来,这事儿一点没错;不过,我仍然怀疑基恩真的认识瘦大个。这么几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他。“他可曾在纽约的拖船上干过活?”
“唔,也许,这事我可说不准。”
“我猜,你可能在西部见过他。”
“也许是吧,我从没去过纽约。”
“唔,这怪我,你竟然认识他,我很纳闷。这个国家太大,不过我想你准认识他。”
“没错,先生,我非常熟悉瘦大个,他只要有一点儿钱,出手就相当大方。一个挺好的、不好对付的人。我在夏延看见过他在工场里一拳就把一个警察放倒在地。”这种事真像是瘦大个干的,他常常在户外练习那种拳式。他看起来就像杰克·登普西,不过是一个喜欢酗酒的年轻的登普西。
“管他妈的是不是他!”我嚷道,风扑面而来。我又喝了一口酒,顿时感到一阵快意。每喝下一口酒,酒力都被灌满敞篷车厢的一股股风给抵消了,酒力在我胃肠中所产生的所有令人舒畅又令人难受的感觉也都被风驱走了。“夏延,我向你奔来了!”我唱了起来,“丹佛,迎接你的孩子吧!”
蒙大拿瘦高个向我转过身,指着我的鞋发表了一番评论:“你一定满以为要是你将它们扔在地上,准会有什么东西生长出来吧?”——当然,说这话时,他一本正经,脸上没一丝笑容,不过,听见此话的其他伙计们都笑开了。的确,我这双鞋可要算是全美国最土气的鞋了;我特意买这种鞋,因为穿着它们在干燥炎热的公路上行走时,我不希望双脚冒汗,除了在比尔山碰见下雨那一次,这双鞋可说久经考验,确实最适合我在路上旅行。想到这,我也同他们一齐笑了起来。瞧,这双鞋现在已破烂得面目全非,有光泽的皮面已经裂开,向上翻卷,活像才绽开的菠萝片,连脚趾头也分明可见。这事不想多提,我们又喝了一口酒,乐呵呵地又笑了起来,犹如置身在梦境中。货车载着我们在沉沉夜色中越过交叉路口的若干小镇,从懒散地行走在公路两旁的、夜晚出来收割的农夫和牛仔身旁开过。他们一齐掉过头来望着我们的货车驰过。
车开出小镇,天色越来越黑,我们看到他们不停地拍打 ... ——在他们看来,我们是一群古怪可疑的家伙。
每年的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的许多人都出来参加收割。来自达科他的两个小伙子此时坐不住了。“我看下次停车小便时,咱们都下车好了;这一带附近看来不缺活儿干。”
“过了这个地方,你们还得往北走。”蒙大拿瘦高个建议,“一直到加拿大,这种活儿不愁找不到。”达科他的两个小伙子漫不经心地点点头;他们对这一建议不以为然。
就在这当儿,离家出走的那金发少年仍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正在像佛教徒那样沉思的基恩如梦初醒,不时地侧身望着疾驰而过、为茫茫夜色所包围的平原,在金发少年的耳边轻语几句。少年点点头,基恩随时在关照少年,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不只是他的情绪,还有他的恐惧及忧虑。我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地方能去,今后凭什么立足谋生?他们没有香烟抽,我掏空烟盒全给了他们。我打心眼里喜欢他们。他们令人感到善良可亲。他们从不向你提出什么要求。我一直希望他们把烟拿去。蒙大拿瘦高个也有香烟,可他从没递上一支。货车又从另一个交叉路口的小镇开过,又看见一群群身穿牛仔服的又瘦又高的男人像沙漠里的虫蛾站在昏暗的灯光下;接着货车向前开,又被茫茫夜色所淹没;头顶上的星星此时显得既明亮又清纯;因为有人说货车现在正以最慢的车速爬上西部高原的一座高山,空气越来越稀薄。山上一片光秃,由于没有任何树丛挡住我们的视线,星星仿佛触手可及。有一次,卡车正在疾驰,我看见公路旁山艾草丛中有一只头部呈白色的奶牛,它那神情怪可怜的。此时卡车平稳加速,那感觉就像乘火车在铁路上行驶一样。
我们的卡车终于又到达一个小镇,车速减缓,蒙大拿瘦高个叫道:“下车小便!”可司机并没理会,一直向前开去,“混账,我要下车!”瘦高个嚷道。
“过来,到车边来解吧!”有人说。
“晤, ... 吗不?”他说。在我们的注视下,他慢慢地、一步一步地移动到车厢后部,臀部靠着车厢一侧想尽量站稳,可双腿仍在晃动。不知谁使劲敲着驾驶室窗,想让开车的兄弟俩留意此事。他俩转过身,哈哈大笑。瘦高个正欲行事,那危险可想而知,就在这当儿司机开始加速到每小时七十英里,方向盘时而向左,时而向右,车身摇晃起来。瘦高个往后退了一步,似乎有所犹豫,接着我们就看见一条水柱喷向空中,仿佛是鲸鱼在喷水似的;他竭力往后挪动,身子下蹲,类似坐姿。司机如法炮制使卡车仍旧摇晃颠簸。乖乖,他无法站稳,小便竟撒向自己身上。我们听见他那因卡车轰鸣而变得有气无力的咒 ... 声:“滚他妈的!……滚他妈的……”仿佛一个旅人爬山涉水后的叹息。他当然不知道这一恶作剧是我们有意干的;他仍然想尽快完事,那着急痛苦的情状真难以言喻。他总算就这样结束了,可衣服已湿得简直可以扭出水来,现在他又得顺着车厢边一摇一晃回到原来的位置,神色难看极了。除了那心情沮丧的金发少年,大家都笑开了;而驾驶室里的明尼苏达兄弟俩更是笑声如雷。我把酒瓶递给他,好让他安静下来。
“他妈的干吗这么干,”他说,“他们可是有意整人?”
“那还用说。”
“晤,怪我不走运。这事我没料到。在内布拉斯加时我也在车上撒过尿,可从没什么不方便。”
卡车不一会儿就到了奥格登小镇,从驾驶室里传来一声“下车小便”,从声音听起来这兄弟俩兴致未尽。瘦高个站在卡车旁边,虽说仍是一副哭丧脸,但此时他还是没放弃这机会,大模大样自便了,仿佛有意要补偿什么似的。从达科他来的两个小伙子向我们告别。看来他们有意在这儿趁收割季节找点活儿干。我们看着他俩消失在夜色中,向着小镇尽头亮着灯光的木屋走去;站在那儿的一个身穿牛仔服的守夜人说有活儿干。我得再买些香烟。基恩和金发少年跟在我后面。我进入的这家店铺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很令我失望。这儿只有一个为当地少男少女准备的类似印第安人用的那种装有龙头的冷饮柜,有几个人正在随着自动点唱机音乐跳舞。我们一进去,音乐声顿时停下来。基思和金发少年站在那儿,没盯谁一眼;他们只需要香烟。那伙人中也有好些漂亮妞儿,有一个冲着金发少年飞送媚眼,可他却没注意到,不过即使他看到了,他也准会无动于衷,他心情一直糟透了。
我给他俩各买了一包香烟,他们十分感激。车快要开了,已是半夜,寒意一阵阵袭来。基恩多次跑遍全国,就是把手指和脚趾一块加起来数,也算不清他跑了多少次。他见多识广,对我们说,眼下最好的办法是用防雨帆布把身子裹起来,不然我们准会冻坏。我们都这么办了,又把剩下的酒喝完,尽管气温越来越低,冷风扎得耳朵很痛,我们仍能保持温暖。在高平原上行驶时,星星似乎格外明亮。卡车已到达怀俄明州了。我仰面躺着,凝视着那深邃的苍穹,心情快活极了,想到我终于远离了那令人心烦的比尔山,尤其想到丹佛即将在我眼前出现,我更加激动——不管我将会在哪儿遇到什么事。这时候,密西西比州的基恩开始哼起歌来,歌声动听、舒婉,就像河水在流淌似的。歌词简单,只是这么几句:“我爱上了一个纯洁的姑娘,她年方十六,可爱又美丽,这世上没有谁比她更纯情。”如此反复,加上了其他歌词,大意是说他一直而且如何思念姑娘,希望再能回到她身旁,可最终还是没见到她。
我说:“基恩,这歌儿真好听。”
“是的,我敢说这是最美的歌儿。”他微笑着说。
“我希望你能到你想去的地方,开开心心过活。”
“我总是到处流浪,从不老呆在一个地方、”
蒙大拿瘦高个一直睡得很香,这时醒过来对我说:“嗨,坏小子,咱们一同先在夏延城逛逛,你再到丹佛,行吗?”
“行。”我趁着酒兴回答,乐意与他同行。
卡车到达夏延城郊时,我们老远就看到地方广播电台上方闪烁着的一片红色灯光,接着卡车便在从人行道两旁拥出的人流中缓行。“真见鬼,咱们遇上了西部狂欢周。”瘦高个说。成群的商人,其中有好些大腹便便,穿着统靴,头戴牛仔高帽,携着放牧女人打扮、壮实如牛的老婆,在夏延旧城木板人行道上前呼后拥;再往前,可见到夏廷新城区中心那直端端的长长大街上一排排街灯。不过狂欢活动主要集中在旧城。礼炮向天空放射。酒店里座无虚席,一直拥挤到人行道上。我着实惊讶,可同时又觉得滑稽可笑,这是我第一次在西部亲眼见到人们如何借助于荒唐的方式来保持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传统。我们得下车同司机兄弟俩告别了;此时,这对明尼苏达兄弟也毫无兴致在这儿久留。同他们说了声再见看到卡车离去,我意识到我将不会再见到同车的伙计了。不过,聚散原来无常,生活就是如此。
“今晚,小心别把 ... 冻坏,”我告诫他们,“那还来得及明天下午在沙漠上烤干。”
“今晚再冷,咱们下了车保管没事。”基恩说。卡车启动了,慢慢从人流中驶过,此刻他们就像包在睡布里的婴孩一样,盯着这个小镇。我望着卡车在夜色中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