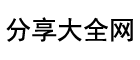太原有个叫张亮的富商,家中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金姑,嫁给城里一个姓李的人,但丈夫早死,金姑年纪轻轻便守了寡。二女儿叫玉姑,许配给城里一个姓曹的人。但因曹某随其父到广东各地去做生意,久久未归,所以玉姑虽已到了出嫁年龄,仍未出阁。
过了两年,附近人纷纷传说,曹某父子在广东沿海某地遇强盗,财物被掠,父子二人也被 ... 死。张亮听了,便与玉姑商量,想让她改嫁给别人。玉姑听后,坚执不允,说道:“大街上的流言蜚语不可信,不如再等一些时日,有个确实的消息。再说我已许配给曹某为妻,怎能再嫁别人。嫁鸡随鸡,嫁犬随犬,曹某若真有个好歹,我也同姐姐一样,守寡便了。”
张亮不听,逼玉姑改嫁,玉姑不再说话。于是张亮唤来媒人,将玉姑又许配了附近一个叫姚平的人,聘礼已送来,吉日已择好,只待人洞房拜天地了。
忽然有一天,张亮家门前急匆匆来了一个蓬首垢面衣衫槛褛的青年人,请求见张亮。张亮来到门前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此人正是前两年传说已死的曹某。张亮忙请他进客厅,置洒席,又令下人们备汤水及新衣让曹某沐浴。
诸事毕后,曹某告诉张亮,自己随父亲这两年在南方作生意。起初非常,但后来忽然遇到一桩公案,结果为打官司花了全部钱财,还受了不少罪,父亲因此心中郁郁不快。竞然一病不起,撒手归西了。临终前嘱咐曹某速回太原。投奔张亮,与玉姑完婚。同时向张亮借些钱财,把自己的棺木运回家乡,不要让自己成了他乡之鬼。
张亮一听,心想,他家现如今是财尽人亡,我将玉姑另嫁他人果然不错,否则跟了这个穷酸过日子,岂不误了我女儿的终身。但眼下发愁的,是怎么想个办法打发了这小子。于是嘴上有一搭无一搭地与曹某说话,心里却打开了算盘。
曹某进门后,张亮家的婢女们都认出了他,于是就有腿勤嘴快的丫环跑到后房告诉了玉姑。玉姑听后,狂喜,拿过剪刀,一刀剪断了与姚平成亲用的红绸,说:“这回可用不着你了。”
到了晚间,玉姑先让随身的小丫环去打听清楚曹某住的屋子,然后趁夜色已深,众人都已安歇,一个人悄悄溜出屋门,来到曹某的门外,轻轻敲了敲。
曹某开门一看,见是玉姑,甚为吃惊。想起古训“男女授受不亲”,急忙欲转身回避,玉姑却一步上前,拉住他的衣袖说:“你不必如此,父母早已将我许配与你,我与你乃明媒正娶,并无见不得人事。但我父如今嫌你贫苦,又为我另选夫婿。我既己聘为君妇,又岂能更事他人?只是现在情势紧迫,我二人如欲结为夫妇,必先私奔,远走他乡。然后寻机而做,仍归父母膝前。你看如何?”
曹某此时尚不知玉姑另嫁事,闻言大惊,拉住玉姑的手细问究竟。玉姑于是将以往从前的事说了一遍,又说自己本意是与姚平成婚当夜,即以布帛束颈 ... ,以示一女不事二夫之志。如今老天可怜,得见曹某,誓与他同生共死,终生厮守。
曹某听罢,长叹一声,两眼发呆,愣愣地好大一会儿没说话。玉姑急问他为今之计,曹某又叹道:“世态炎凉,人情薄如纸,也就不去管他了。只是我如今穷愁潦倒身无分文,纵想携你远走高飞,又如何能够呢!”
玉姑听罢,微微一笑道:“郎君不必忧虑,我平时多有积蓄,现已随身带来。我二人即便行万里路,钱财也花费不尽。”曹某听了,面上刚有喜色却又一脸疑云。
玉姑忙问缘故,曹某说:“虽然盘缠有了,但来日方长。你是千金小姐,而我今日则已沦为一穷汉。况且瞻望前程,也不见有一丝半点儿的光亮,假若我终生都是而今这付穷模样,又怎能养活你这位娇小姐?”
玉姑正色答道:“你也太过忧虑了,哪里有男子汉大丈夫一辈子郁郁不得志,穷愁落魄呢?再说,我方才已言明自己从一而终,穷也罢,富也罢,我一辈子守着你就是了。”
曹某听了,虽受感动,但仍犹豫不决。玉姑恐时间长了,被人撞见,于是不断催促他,曹某这才和玉姑收拾了东西,趁黑夜从后花园的角门溜了出去。
在路上,他们商议先投奔玉姑的姐姐金姑家,到那里先躲一躲,然后再徐图计议。到了金姑家门口,将门一打,里边有个丫环问:“谁呀?”玉姑说:“我是玉姑,我姐姐金姑在吧?”这时金姑也已走到门边,但并未开门,只是问道:“妹妹这么晚来有什么事?”玉姑不加掩饰地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金姑寻思了一会儿,隔着门说:“你和曹郎远走他乡,我也赞同。只是父亲发现你们逃走后,十有八九首先会到我这里来寻找。依我之见,你们不如快快到别处躲藏。如果在我这里藏身,无异自投罗网。”玉姑听罢,觉得姐姐说的十分有理,于是隔着门谢了姐姐,与曹某又投别处了。
张亮正在家中睡觉,忽然有丫环敲门来报,小姐不见了,家中遍寻不着。张亮急忙披衣下地,出门察看。这时有仆人慌慌张张前来说,曹某也失踪了。张亮一想,准是二人趁夜私奔,不禁勃然大怒。他唤集仆人,准备前去捉回。张亮寻思他们第一个落脚点恐怕就是金姑的家,于是带众人齐扑金姑家而来。
到了金姑家把门一敲,金姑又来到门边,问是何人。张亮唤女儿开门,并把玉姑私奔的事说了一遍。但金姑并不开门,只是回答道:“刚才妹妹果然和曹郎一同来到我家,求我藏匿,但我没有应允,他们已经往别处去了。您率众人快去追赶,一定能追上。”
张亮听后并不相信,又见金姑不肯开门,心中更是生疑,于是说:“他们一定藏于你处,速开门,不要再为他们支吾。”
金姑也忿忿然说:“逃走的人你不追,非要进我家干什么!”
张亮怒火中烧,举鞭打门说:“再不开门,便破门而入!”
过了好一会儿,金姑才将门打开,张亮率众人一拥而人,四处乱翻乱看,竟然空无一人。张亮心里不禁十分懊丧,心想金姑也许真的没有收留他们。
就在张亮率众人准备离开时,他忽然抬头看见金姑坐在一只大木柜上,一动不动,也不起身相送。张亮生疑,要打开木柜看看究竟。金姑却说:“这个柜子封锁已有多年,且年深日久,钥匙也早已丢失不见,没办法打开。”
张亮大喝一声道:“住口!奸人必在其中。”令仆人们将木柜抬回。金姑拦阻不住,只能眼睁睁地瞧着木柜被抬走了。
张亮率众人将大木柜抬回家,用铁棍撬开一看,不觉同时发一声喊,一个个目瞪口呆:原来木柜中躲着一个浑身 ... ... 的和尚,而且口眼紧闭一动不动,已然死了!众人这一惊可非同小可,纷纷议论道,原只是去捉人,如今却弄出一场官司来。
张亮紧锁眉头思前想后,突然得到一条妙计,不禁变忧为喜。原来他想两日后玉姑就将与姚平成婚,现而今玉姑脱逃,不知何往。正苦于无法向姚平交待,不如就将这死和尚乔装打扮,穿上玉姑的衣服入殓,告知姚家玉姑忽患暴疾而亡,岂不是个绝好的主意!想到此,即令仆人们将死和尚从柜中取出,给他穿上玉姑的衣服,头顶带上女人的假发髻,然后停尸堂中。并即刻派人去附近寺庙请来和尚,念经超度,又同时派人去姚家,告知玉姑暴死,因为时辰不好,所以不能拖延时日,必须在天色微明时即入棺,姚家不必来人了。这样安排了以后,张亮自以为得计,安称合来,也顿时觉得困倦无比。于是他吩咐了家人们几句,自己便回房去歇息了。
灵堂里,请来的一群和尚念念有词,喋喋不休。旁边的仆人们因为跟着张亮东奔西跑,个个腿软筋麻,睡意朦胧,听着和尚们千篇一律的诵经声,更使人昏昏欲睡。不久,灵堂里的诵经声和鼻息声即响成一片,此起彼伏,除此以外,倒是一片寂静。
然而就在此时,在暗淡的烛光下,只见棺中的死和尚似乎动了一下,几个和尚大为惊讶,疑心自己因困倦看花了眼,揉揉眼再看,却见那死和尚又动手又是抬脚,冷不丁的,竟然一下从棺中坐了起来。他的身影映在被烛光照得恍惚迷离的慢帐上,显得分外高大,狰狞、恐怖。
诵经的众和尚大叫起来,抱头鼠窜,这时仆人们也被惊醒,一见那死和尚正欲从棺中走出,不禁齐声大喊:“炸尸了!炸尸了!”纷纷跑进旁边的屋室,并把门牢牢拴上。这下却害了念经的众和尚,他们摸不着门路,不知到哪里藏躲,东奔西撞,最后总算摸到了大门,哄嚷着逃了出去。随身携来的各种念经超度用的法器也丢了一地,狼狈无比。
原来这棺中的和尚并未死去。只是当时昏厥而已。这和尚是城中一座大寺庙的僧人,因为几次到金姑的家里去,为金姑的亡夫作超度而认识了金姑。金姑长得虽不是天资国色,却也有几分模样,和尚见了不觉心动,意欲将她勾引到手。金姑生性风流,却又青年守寡,长夜难熬,心里也早有意思。两人一来二去,眉目传情,不久便成了好事,难舍难分。当天夜里玉姑前来投宿时,金姑正与和尚行云雨之事,所以不能开门,将玉姑拒于门外,并花言巧语将玉姑支走。等到张亮来后,定要进门,金姑无可奈何,只好将和尚藏于木拒中,暂且躲避一时,没想到张亮竟带人将木柜抬走。
和尚事出意外,十分恐惧,加上在木柜中闭置的时间太久,无法喘息,所以昏然如死。在灵堂中被风一吹,渐渐苏醒,于是伸手抬腿,坐起身来,看见众人狼奔鼠窜,不知何故。环顾四周,见有许多哀词纸钱,自己身下躺的乃是灵床,不觉自问道:“我是死了吗?”掐掐大腿,疼,知道自己未死,放下心来。继而低头一看,见自己身上穿着女人的衣服,心里更加诧异。他抬起身子,想站起来,又觉得两脚不象平时那么自如,低头看去,原来脚上穿了一双女人的小脚鞋,难怪又紧又尖。和尚把鞋脱了,扔到一边,光着脚摸出大门,想回到自己住的寺庙。他走了一会儿,见旁边有一豆腐店,里边灯光明亮,磨豆腐的声音不绝于耳。和尚觉得十分口渴,于是上去敲门求些水喝。
豆腐店的店主姓莫名五,打开门一看,见外边站着一个身穿华丽服装的女子,心想她恐怕是哪个大户人家逃出来的小妾。莫五将和尚带进门,刚要给他倒水,莫五的女儿却叫起来:“这个坏男人,假扮成妇女的样子,要干什么!爹爹你老眼昏花,连男女都认不出来,还把这个坏家伙往屋里带呢!”
原来莫五的女儿虽然只有十五岁,却乖巧聪慧异常,一眼便看穿和尚是个男人,故此喊叫起来。莫五一听大惊,顺手抄起一根棍子,上前就揍。和尚忙跪地求饶,愿意把身上穿的戴的都留下。于是莫五找了一身布衣和布鞋,和尚则脱下女衣及首饰。莫五催和尚换好衣服后,即将他赶了出去。
和尚垂头丧气地往庙里赶,快到寺庙时,忽然见月光下路边蹲着一个女人。再仔细一瞧,原来这女人是屠夫王二的媳妇。屠夫王二的家就住在寺庙旁边,所以和尚认识王二和他媳妇,走近前去,才发现这女人正在路边草丛里小解。
王二的媳妇生得有几分姿色,又善调情,平时和尚对她就十分有意,只苦于没有下手的机会,眼下正是天赐良机。和尚于是快步上前,王二的媳妇初时吓了一跳,及至看见是和尚,倒安下心来。和尚边调戏边动手脚,王二媳妇也不大推拒,于是和尚搂着她进了王二的家,二人上了床,便翻云复雨地快活起来。
二人正在销魂之际,忽然大门一响,王二却回来了。见二人正在难解难分,王二大怒,举刀扑来,和尚大叫饶命,王二哪里肯听,一刀结果了性命。王二又举刀欲 ... 女人,女人跪地连连求烧,反正和尚已死,死无对证,女人就说是和尚逼她如此。王二被女人花言巧语如此这般地一说,也软下来,遂放了女人一条性命。
原来王二每天天未亮时即肩挑猪肉赶到市场,今日走了不多远,忽想起忘记带秤,所以急匆匆返家取秤。没想到正撞见和尚弄他老婆,一时大怒, ... 了和尚,然后乘夜将和尚尸体扔到寺前井中,自己依旧到市场上去卖肉。王二卖完肉后返家,只听街坊四邻纷纷在那里说,寺前井中发现有一和尚尸体,现已报官,官府马上要来查验,井邀王二同去看热闹。
王二一听,不觉两腿发软眼也花了起来。心想万一官府要查出是我做的,可怎么是好。心里一怕,便干脆收拾东西,悄悄溜出家门,一走了之。王二后来逃到交城,开了个酒铺谋生,虽是小本生意,买卖倒还红火。常来的众多酒客中,有一美少年,他三天两头常来喝上三杯两盏,赶上店里客人不多时,王二也常过来陪他喝一会儿。一来二去,二人相熟起来,无话不谈。有次王二喝醉了,无意中说出了自己 ... 死和尚一事。少年听了,也不置可否,只是点头而已。
这位少年正是玉姑的丈夫曹郎。原来曹郎之父临终前,曾拉着儿子的手,流着泪说:“人情冷暖,大都是凭着贫富而定。我死后,你去投奔玉姑的父亲。如果他能收留你,不悔婚约,你就算有个安身之处,不用到处飘泊。万一他嫌你贫困,不肯接纳,我还有个朋友你可去投靠。他就是交城县县令陈公,他与我为生死之交,我想他断断不会把你拒之门外。”言毕,伏枕上作书。书罢,交与曹郎,又说:“拿着我的书信求见陈公,他一定会帮助你,但你也要勤谨努力,好自为之。”说罢,长叹一声,魂归九泉。
所以曹郎和玉姑出逃后,便投奔陈公来。曹郎假称自己已娶妻,而妻家贫无立锥之地。故随自己一同前来。陈公果然念旧,留曹郎在府中做个文笔小吏,但对他的薪律从优,从此曹郎和玉姑总算有了安定的生活。一年多后,陈公从交城县令升任太原知府,曹郎也随其同往。
陈公到任后,审理前任留下的积案,其中一件最为棘手的就是和尚被 ... 案。
原来自从井中发现和尚尸体后,前任太原知府便亲加勘验,他见和尚身上穿着普通人的衣服,不禁心中生疑,道:“和尚应身着僧衣,现身穿布衣是何道理。”于是令附近百姓们辨识。有人认出这是莫五的衣服,便向官府举报。于是捕吏们将莫五收捕,认定他有 ... 人嫌疑。莫五大叫冤曲,捕吏们不听,搜其家,欲得凶器。不想凶器未得,却搜得华丽的女子衣服和金银首饰若干。
知府认为莫五开个小豆腐店勉强糊口,家中不应有这等华贵器物,其来历定有问题。这时张亮家炸尸一事,也已由里正报官,知府怀疑衣服手饰是女尸身上的穿戴。传张亮上衙门一认,张亮连说:“正是小女的东西,正是小女的东西。”于是知府让张亮与莫五对质,莫五仍称冤枉,说:“昨天夜里我正在磨豆腐,忽然外边有人敲门,开了一看,见一身穿华丽外衣的女子站在门前讨水喝。我将他引进屋,觉察他是一个男人,心想他男扮女装肯定心怀不良,举棍要打,他却跪地求饶,愿将身上的所穿之衣及一首饰与我换一布衣布鞋。我与他交换后,他即出门不知所往。我怎么会知道这是张亮家的衣物呢。”
张亮听了,虽然明知莫五说的是真情实活。却不敢承认那女尸其实就是自己用和尚装扮成的。因为那样一来,自己就成了 ... 死和尚的凶手。于是他一口咬定,说:“我女儿明明死后又炸尸,怎能说她死后又变成一个和尚!我想一定是死人炸尸后到处乱跑,跑到莫五家门口又僵仆于地,莫五趁机扒走我女儿的衣物。”
知府于是对莫五用刑,起先莫五还咬牙忍着,无奈“人心似铁,官法如炉”,几次大刑过后,莫五怎么咬牙也无济于事了。只好承认自己 ... 了和尚。再动刑,又承认自己扒走了女尸的衣物。问将和尚尸体扔到何处,凶器在哪儿,莫五却又信口胡编,说不出个所以然。因此官司拖了一年多,至今未决,成了一件悬案。
近来知府因为某事被御史参了一本,朝廷将其罢免,陈公继任,审理积案,看到这件案子时,认为莫五已是一个年近六十的老人,一夜之间又 ... 人又掠物,不合情理,其中必有可疑,于是叫集手下的文书们共同商量。曹郎阅着宗卷,见案件发生的年月日后,大为惊讶,回家后告诉玉姑。玉姑听了,也说:“此案发生的月日,正是当初你我逃亡的当夜。案中又有我的衣服首饰,必与我有关,你将卷宗取回家,待我细观。”
第二天,曹郎将卷宗取回,交与玉姑细看,看毕,夫妻二人慢慢推想猜测其中的缘故。玉姑说:“当日我既然与你私奔,父亲寻我不获,也许会向姚家人托词说我暴死,以了结婚事,这倒很是合乎情理。但又哪里来的什么炸尸,使人迷惑不解。”玉姑以手托腮,想了半天忽然叫道:“有了!我父既然向姚家人谎称我已死,却又苦于没有尸体,一眼便会被人看破,于是以重金贿赂和尚,让他穿上我的衣服,戴上首饰,伪装成女人
然后等夜深忽然起立,诈为尸变而逃走。半途中口渴难忍,却忘记自己身穿女服而叩门求饮,这也在情理之中。如此说来,莫五以前的供词是真情实话。那么 ... 死和尚的又当是准呢?”
玉姑又略想了想。将手掌轻轻一拍,叫道:“必是我父亲!他怕僧人走后,泄漏了秘密,所以又暗暗派人将其追 ... 。如此,此案可结,只分可怜我的父亲。”
曹郎听后,沉吟半晌,忽然拍掌大笑道:“说的对,真是一语道破天机,依你所言再加推断,那些请来念经诵佛超度死人的和尚们,三天两头见死人,岂有认不出活人死人的道理!如此看来,必定这些诵经的和尚们也被你父亲买通,众人暗中相互照应,以诈尸遮人耳目。至于 ... 死和尚的凶手,我早已知道是谁,并不是你的父亲,你不必担心。此案马上就要真相大白。”
第三天,曹郎向陈公将事情经过以及他和玉姑的推测详述了一遍,陈公当即升堂,传张亮问话,问张亮案发当日情形,张亮仍供述如前。陈公又问:“你女得何病而亡?”张亮答:“暴疾而亡,不知何病!”陈公再问:“诈尸后,尸体跑到什么地方?”张亮低头答道:“这应当问莫五。”陈公笑道:“此事不须问莫五,我还你女儿如何?”言毕,即派人请玉姑出见。玉姑缓缓来到堂中,立于书案之后,远远地朝张亮拜了一拜。随后又向张亮说:“案已大白,爹爹不要再事遮掩,自讨苦吃。”言毕,又款款地走到屏幕后边去了。
张亮大惊失色,于是将当夜发现女儿私奔,去金姑家索讨,搬回木柜,柜中有一死和尚事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陈公即时派人传来金姑,问柜中和尚是何来历。金姑身至州衙,已是胆战心惊,丝毫不敢隐瞒,于是将自己与和尚私通事供述出来。至此,全案真相大白。
陈公派人依曹郎指点的地方去捉拿王二,不几天,差人从交城将王二带到。陈公升堂一问,王二不打自招,陈公将其打入死牢,此案遂结。从此,陈公断狱如神的美名开始在当地传扬开来,而其实此案所以能破是靠了许许多多的巧合和偶然,这就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