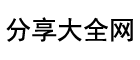章培恒的个人简介
章培恒,1984年被国务院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6年先后获得复旦大学首席教授、杰出教授称号。现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兼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章培恒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6月7日凌晨在华山医院逝世,享年77岁。2018年5月,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公布了首批“上海社科大师”人选名单,章培恒当选。人物简介
章培恒先生先后受教于朱东润教授和蒋天枢教授;在注重理论阐释上,则受益于贾植芳教授。 1952年秋,他因院系调整而由私立上海学院中文系转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这正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黄金时代,名师荟萃。他一进复旦,就受到了朱东润、贾植芳教授等的熏陶。朱先生是一位不受权威束缚、敢于并善于独立思考的专家,当时教他们古代文学,对当时的很多主流见解都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而且都有自己的依据。如对于《诗经·国风》出于民间的这种几乎为学术界所公认的说法,朱先生就作了十分有力的批驳。这使他很感振奋,并把这种治学精神作为自己的楷模。而朱先生对他也十分赞赏,在其所撰《自传》中曾有生动的记述。 1956年秋,章先生作为中文系的助教,开始接受蒋天枢教授的指导。蒋先生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是陈寅恪先生的入室弟子,以治学谨严,不曲学阿世,而为陈先生所赏识和信任,后来并将保存和编刊自己全集的重任托付给他。他要章先生先从历史和语言学方面打基础,以三年时间读《说文》段注、《尔雅注疏》、《尔雅义疏》和《方言》,同时读《通鉴》,校点“前四史”,泛览目录、版本、校勘学方面的著作,从《汉书·艺文志》直到《书林清话》。这使章先生走入了一个新的学术境界。虽然学得很艰苦,但却取得了很大收获。所以后来日本著名学者伊藤漱平教授在论及复旦大学研治元明清文学的专家时曾说:“从师承来说,在复旦大学曾师事硕学陈寅恪博士的高弟蒋天枢教授的章培恒教授,与赵景深教授的学风有别而独树一帜。他的本领在于以目录学、书志学为基础,先提出大胆崭新的假设,再努力加以证实。”另一方面,他从1952年起就向贾植芳教授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而且还由此懂得了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的重要性。他在读高中时就不止一次地读过鲁迅的小说集和杂文集,此时又系统地读了新文学开始以来直到30年代的著名文学作品,还认真地读了胡风的八本论文集。后来他虽转而研习古代文学,但对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仍很感兴趣,并反复地研读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原著。他自己说,他在对古代文学的评价、阐释上,常常提出一些与时贤不同的见解,实缘于他的这种学习经历。
人物年表
1934年1月8日生于浙江绍兴。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参加中国共产党。 1954年1月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并任教至今。 1980年12月任教授。 1983年至1985年间任中文系主任。 1984年被国务院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1985年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同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1996年先后获得 复旦大学首席教授、杰出教授称号。 2011年6月7日凌晨在华山医院逝世,享年77岁。
社会兼职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第二、三届),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家教委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 章培恒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先后开设中国文学史(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明代文学研究、中国哲学与文学、西游记研究、中国小说史、古籍校读法等课程。承担指导中国古代文学(元明清文学)的博士生、硕士生和中国古典文献学(古籍整理) 硕士生的任务。
学术成果
概述
章培恒先生主要学术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历年发表的一百余篇论文,大多已收入《献疑集》(岳麓书社,1993)、《灾枣集》(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和《不京不海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三书中; 二是以专著形式发表的《洪升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中国文学史》(主编之一兼作者,复旦大学出版杜,1996)和《中国文学史(新著)》(第一主编兼主要作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三是由他单独主持或与其他专家共同主持的大型集体项目如《辞海》的中国古代文学分科、《新编明人年谱丛刊》等。
专著
1979年出版专著《洪 升研究》,对清初戏剧家洪升的生平作了系统的考订和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该书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和中国戏剧家协会理论著作奖。 章培恒教授与骆玉明教授共同主编了《中国文学史》,1996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学术界和读书界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一种突破。 后又编成《中国文学史新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从人性发展的视角对中国文学史进行描述,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突破,具有广泛影响。 1985年编纂《全明诗》(集体科研项目),上海古藉出版社陆续出版。1979年修订《辞海》他担任分科主编(负责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和编委。合编大型丛书《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藉出版社出版)和 《近代小说大系》(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主编《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巴蜀书社出版),《中国禁书大观》(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其中的《中国禁书简史》 (己由日本新潮社出版日译单行本),《新编明人年谱丛刊》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章培恒
论文
论文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考证性的,其所提出的看法大都与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见解有相当大的距离,如关于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解放后的中国研究学者都已肯定为吴承恩,他却认为吴承恩所作《西游记》为游记性质的作品而非通俗小说,发表了《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等几篇论文加以论证。中国现已有部分研究者接受他的观点。此类论文中的大部分收入其论文集《献疑集》,于1993年由岳麓书社出版。该书曾先后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和国家教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 另一类论文是对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重新加以剖析(上起先秦,下迄近代)。其所得出的结论,或为以前的研究者所未尝言及,或与流行的见解相歧异。前者如《金圣叹的文学批评》、《中华文史论丛》 第三辑,与人合作),联系金圣叹的哲学思想以研究其文学批评,为前人所未及;后者如《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日本《古田敬一教授退官纪念中国语言文学论集》),将李梦阳作为晚明文学新思潮的先驱,与通常把李梦阳仅仅视为晚明文学新思潮的批判对象的观点大相径庭。这些也都为同行所重视。
书评
《明代徽州文学研究》――一部地域性文学研究中的优秀之作(《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8月4日) 不尚空论,言必有据――读谈蓓芳《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论考》(《文学报》2006年12月28日)
杂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古籍整理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04期) 独立思考与细心求证(《光明日报》2000年8月10日) 不能欣赏昆曲是知识分子素养上的缺憾――关于保存和复兴昆曲的几点设想(《文汇报》2001年8月18日) 规范文科学术刻不容缓(《中国高等教育》2001年12期) 关于建立学术规范的两点建议(《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01期)
序跋
《三国演义辞典》前言(《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02期) 《三国演义辞典》序(《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02期) 对武侠小说的再认识(代序)(《武侠世界的怪才――古龙小说艺术谈》,曹正文著,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年) 《全明诗》前言(《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05期) 《江盈科集》序(《书屋》1997年04期) 人性的解放与形式的演进――《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序(《文汇报》2007年7月17日)
访谈
美好的中文(章培恒、陈村,《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05期) 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贯通――章培恒教授访谈录(章培恒、宋荣,《语文教学与研究》2004年22期) 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章培恒先生学术访谈录(章培恒、马世年《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01期)
学术述评
洪升研究
章先生独立从事关于文学史的个案研究是从1957年开始撰写《洪升年谱》而起步的,这同时也是他进行实证研究的首次尝试。尽管当时学术界已开始关注清代成就最高的两大戏 曲家,但有关洪升的生平交游、思想著述等基本问题,尚无人作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为全面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先后自费去北京、南京、杭州等地搜集到大量罕见资料,然后辨伪订误,五历寒暑,终于在1962年完成全书。该书“引用书目”达246种,通过认真考证和排比,不仅首次全面细致地胪叙了谱主的家世背景、个人遭际、思想著述、亲友关系等,而且还就洪氏“家难”、洪升对清廷的态度以及“演《长生殿》之祸”等诸多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看法,把对洪升及其剧作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稿尘封了十七年之后,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但当时仍属于学科前沿性质的成果,因而立即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称扬它“搜罗宏富、取舍谨严、考订翔实,论证有据”,1980年版《中国百科年鉴》将其列入1979年出版的研究中国文学遗产的四部优秀著作之一。
文学史重要个案研究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学术研究逐渐走上正轨之后,章先生继续瞄准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个案,上溯先秦两汉,中探六朝唐宋,下迄元明清,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上下求索,仅就微观考证而言,就发表了三十多篇论文。由于这些文章或是向既有定论挑战,或与时论相左,或发前人所未发,因而往往会引起热烈的讨论,这不仅促使本学科相关领域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而且对于改革开放初期学术领域的拨乱反正和后来引导学风从浮躁走向求实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考证《聊斋志异》的写作年代,撰有《聊斋志异三会本·新序》、《〈聊斋志异〉写作年代考》、《再谈〈聊斋志异〉原稿的编次问题》三文,指出通行的十二卷本和十六卷本都是后人所编,唯原稿本共八册,是作者按写作先后排列的,原稿中的四册虽已佚失,但通过对铸雪斋抄本的研究仍可以考订出正确的次序。然后考定该书前后写作历四十年馀,并进而推考出原稿各册写作的大致年代。 其次,还有一类是对于先秦至唐宋辞赋诗文作家作品疑案的考证。如《关于屈原生平的几个问题》、《李白的婚姻生活、社会地位和氏族》皆提出独到见解,但影响最大的还是对北宋几位作家的连环案的探讨,共撰文三篇。 章先生就文学史个案进行理论阐释是从1962年秋开始的。在这方面他最重视的,是与刘大杰先生合撰的《论金圣叹的文学批评》。该文原本是为刘大杰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而写的一节,由刘先生改定;因全文从论点的确定到形诸文字都主要是他独立完成的,所以作为论文于1963年5月单独发表时二人一起署名,后来刘夫人李辉群女士编《刘大杰古典文学的论文选集》时则未收入。 与此同时而就古代文学一系列个案所进行的理论剖析,章先生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各个案的主体(含某作家群或某个时代的作家)是否“比他们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而这些“新的东西”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正是那些与五四新文学相通的各种因素。因此,其所论述也都往往与当时的主流观念相左。就所选个案的分布而言,以明清文学最多,论文达十多篇,如1983年发表的《论〈金瓶梅词话〉》和《试论凌?初的“两拍”》、1986年发表的《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等。
重写文学史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重写文学史”的思潮,在中国大陆学 术界荡漾了多年,讨论的文章连篇累牍,实践的成果也纷至沓来。章先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1987年承担了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作为全国自学考试教材的任务,随后还应邀在《上海文论》主持对古代文学重加研讨的栏目,从而开始了建构文学史的思考和实践。上述论文中,有一部分既是这种思考过程中的成果,也是在为其建构文学史作准备。随着文学观念的更新和结合一系列个案研究而进行的思考,“文学的进步与人性的发展相联系”这一理念日益明晰,最后被确定为描叙文学史的基本线索。全书竣稿后,于1993年底由国家教委自学考试委员会中文学科组专家进行审查并获通过。但后来觉得该书对自学考试不尽合适,所以干脆改作独立的著作交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著以马克思主义人性观为指导,重新审视和建构中国文学史,卷首的《导论》对文学的性质和文学发展的主线都作了截然有异于国内一般文学史的深入论述,书末《终章》则讨论了元明以来的文学发展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无论是文学史观,还是对文学史的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都有许多独到的认识,令人耳目一新。打破了文学史研究的旧模式,开创了文学史研究的新格局和新境界。因而在当年举行的专家研讨会上,既称它为“石破天惊”之作,也指出其不足之处。随着新书的上市流播,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荡,报道评论如潮。但他很快就感到了此书的重要缺陷:没有从文学的艺术特征的角度(他又称之为形式的角度)来探讨和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也未能较具体地显示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联系。其后他读了《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发表的孙明君《追寻遥远的理想――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回顾和瞻望》一文(该文既肯定了复旦版《中国文学史》的出版“标志着古典文学研究打破了旧的思维定势,完全走出了政治因素干扰的时代,使文学研究进入了自由的新天地”,又指出其“距离人们的期望尚有一定的距离”,例如“分期的标准依然是取决于王朝的更替”等),认为其批评深中肯綮。 章先生本是一位既执着地坚持真理,也敢于修正谬误的学者,通过深思熟虑之后,他毅然决定再次重写《中国文学史》。但此次的重写不仅要继续突破文学史研究中的旧模式,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首先从思想观念上突破自我。因而他曾就文学的功能、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文学与人性的关系、人性的发展与文学的艺术形式及其美感的发展的关系、文学史的分期、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过深入的反思检讨,然后重组生力军从事新的攀登,才重新建构了独具特色的文学史体系,其成果于1998年以《中国文学史(新著)》为书名梓行于世,成为与“前著”(指复旦版《中国文学史》,下同)不同的另一著作。
学人轶事
蒋天枢对章培恒的影响很大,不光是学术方面,还有言行处事。 章培恒先生回忆“四人帮”粉碎时,古籍出版社要蒋天枢帮忙编纂陈寅恪的文选,事后给了蒋天枢1000多元稿费。当时蒋天枢先生在学校的工资是200元一个月。1000多元相当于小半年的收入。但是蒋先生严辞拒绝了这一笔当时的巨额稿费,理由只有一个:学生替老师编书,怎能收钱? “文革”时期,陈寅恪怕自己的文稿被抄走,著作从此失传,便把文稿做了备份寄给蒋天枢,要蒋天枢先生帮忙保存。“文革”之后,陈寅恪的视力状况不好,蒋天枢便一肩担起帮陈寅恪重编文稿的责任。“蒋先生自己的许多著作在‘文革’时也被抄走,‘文革’后也该先编自己的书,可是他将自己的书抛在一边,把全部的精力用在整理陈先生的稿件上。”章培恒说,语气敬佩。 蒋天枢尊师已经到了一种近乎偏执的地步。蒋天枢与陈寅恪有师生之谊,对王国维自然也是严执弟子礼。同行或学生“王国维长王国维短”,即便满贮崇敬之情,都有引起蒋先生侧目之虞,在他看来,说“王国维先生”已经大不敬了,何乃直呼其名也!至于他,当然恪守旧例,开口闭口是“静安先生”。 当时朱东润算来是个高调人物,好发警言奇语,一次假工会礼堂开会,说到得意处他老人家神采飞扬起来,大概随意说了陈寅恪什么什么,未见得有不敬之意。还没等在座老少反应过来,蒋天枢先生从人群中拔起,指着朱先生哼哼了几句,便拂袖而去。在平常的日子里,据说难得看到朱东润先生难堪,这回给他的倒是十足的难堪。朱先生唯有啧啧几声,并哭笑不得地摊摊手。 中文系已故的教授许道明先生在回忆章培恒和蒋天枢的文章里有这么一段:“蒋天枢先生的高足章培恒教授算来已是当今沪上学术大腕了,他从他的老师那边得到了许多做学问的道道,当是无容争辩的。此外,他显然还是一个上过‘尊师’课的人。记不清何人向我谈过,一天,章先生随蒋先生外出办事,晚间完事后,他照例陪送老师归家。途中来了一场大雨,车到第一宿舍大门,遍地清湿,而蒋先生脚上套的却是家常的布鞋。学生背老师,是章先生的最初提议,自然被蒋先生坚拒。那年章先生的年岁好像也已直逼花甲,安全第一嘛,弄不好两个老头,一老一小跌成一团,终究不是好玩的。于是,老师蒋天枢跨出车门,松爽地进了大门直奔寓所,学生章培恒脱下皮鞋,一手拎着,在黑夜里穿着一双白袜跟在老师的身后。”
获奖情况
《洪升研究》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和中国戏剧家协会理论著作奖。
1980年版《中国百科年鉴》将其列入1979年出版的研究中国文学遗产的四部优秀著作之一。
《献疑集》曾先后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和国家教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 1984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1996年先后获得复旦大学首席教授、杰出教授称号。
2018年5月,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公布了首批“上海社科大师”人选名单,章培恒当选。
相关链接
教授章培恒:以“人性”修文学
1996年《中国文学史》上市流播,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荡,报道评论如潮。对于“石破天惊”之誉,章培恒有清醒认识:所谓“石破天惊”也不过是肯定了它的开创性,但与文学史的应有任务――对文学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的描述――还有很大的距离。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毅然决定重写《中国文学史》。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各种指责纷至沓来,认为这么快就重出一部是为 了捞钱。 1998年年初和年底,《中国文学史新著》第一卷、第二卷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当时教育部正拟推荐若干供大学文科使用的教材,经专家评审后,该书虽未出齐和上架,但已被列入重点推荐的教材。 可惜的是,章先生在1999年被查出患了癌症,第三卷的出版因此搁置下来。这成了他的心头大事。《中国文学史新著》另一责编韩结根说,章先生在病房里也一直没有放下手头的工作,因此这部新著的不少统稿工作,是章先生在住院期间逐步完成的。2005年,章先生身体略为好转后,完成了第三卷的写作,并重新修改了第一卷、第二卷。皇皇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宣告完成。 个人著史,似乎是复旦大学文史专家的传统和情结。周谷城著《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皆可说明这一点。往后,还有葛剑雄撰《中国人口发展史》等不一而足。章培恒先生之于《中国文学史新著》,名义上是主编,实际上是继承了复旦大学文史专家个人著史的传统。这一点未必为章先生所认同,但相信很多人会作如是观。
琐忆
淡泊超然心境对待死亡的来临
尽管对恩师章培恒先生的病情有思想准备,但这一天的到来,还是让我感觉有些突然。6月6日中午接到同事打来的电话,说先生病危,我紧急赶到他入住的华山医院探望。在同事的提醒下,章先生勉强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但已无力言语。此时的先生高烧不退,心跳甚快,整个身体斜躺在病床上,面容憔悴,极度消瘦,让人很难将其与往日精神矍铄、风度不俗的他联系在一起。次日凌晨,经不住病魔无情的摧折,先生还是匆匆走了。
先生在2000年上半年被确诊患前列腺癌,从那时起直至去世的十余年间,他频繁进出医院,病情几度反复,饱受病魔的折磨。然而,先生对于生命所表现出的独特的体悟与态度,点点滴滴,让人无法忘怀。
人活着既要有质量又要有价值,这可以说是先生一贯秉持的一项生命准则。回想起十余年前,我从医院取回他的肿瘤病理报告单,与同事一起惴惴不安地走进他的办公室,想方设法把病情说得委婉一些,以为这样可以避免刺激到他,而先生从我们的表情和语气中似乎已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要求我们如实告知诊断的结果。想必是他希望真实了解自己的病情,以便作出相应的特别是研究工作上的安排。事实上,在以后频繁的检查和治疗中,他每每会仔细查看各类检查的单子,要瞒也总是瞒不过他的。
虽然身患恶疾,但先生却更加忘我地投入到他的学术研究中去。在患病期间,先生将相当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以增订他和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以下简称《新著》),不仅在1998年出版的《新著》上、中卷的基础上,完成了下卷的撰写,而且对原版的上、中卷又作了相应的修订。即便是在《新著》增订本于2007年出版后,局部的修订工作仍在进行。当时,由于癌症的扩散,先生的腿部严重肿胀,坐与站都很艰难。但据他的助手透露,先生还是坚持将全书的五百余条引文又重新作了校订,对书中的若干小节也进行了重写。
先生是一个追求完美、自我要求近乎苛刻的人,确切地说,他是极尽自己生命之能量来完成这部《新著》的增修。他曾说过,一个人想在学术上作出一番成就,往往是要付出健康代价的。这句话也从侧面反映出先生的人生信条:即视学术为生命,并在追求卓越中真正体现生命存在的价值。正因为如此,即便是在癌症扩散、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先生也没有停止过思考和工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头脑就像一台开动的机器,一直处于运转的状态,似乎总是有想不完的问题。
先生病重住院之际,我有几次前去陪伴照顾,言谈间,他常常会主动挑起研究上的一些话题,兴致颇浓。有时实在讲累了,就说:“我先睡一会儿。”等到醒来稍有精神,又会接着聊下去。听他的助手说起,今年3月间,先生一度自感病情严重,所剩时间不多,虽然身体状况很差,却还想着如何尽快廓清他长时间思考的有关《玉台新咏》的若干问题。在这种时候,别人想劝他也是劝不住的。他显然不愿浪费时间,不想给自己留下太多的遗憾,能做一点是一点。这是先生的作风,也是他在有限的人生旅程中享受生命的一种独特方式。
然而,先生又是一个非常热爱生命的人。被确诊为癌症后,他始终积极配合治疗,即使是在2008年以来癌症逐渐扩散的情况下,也从未轻易放弃。尽管在后期的治疗中一波三折,吃了不少的苦头,特别是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病情加重,胃纳较差,为了增强体质对抗病魔,他总是坚持让自己多吃些东西。有几次在医院陪伴先生,看得出他其实没什么食欲,有时甚至对着一小碗面条也发愁,即便如此,他还是尽力而为,哪怕是勉强吃上几小口。为活动身体和帮助消化,有时在用餐后,他也会让人搀扶着在病房的过道上步履艰难地慢走一圈,而回到病房,往往已是气喘吁吁、心跳加快,用他的话来说,就像是正常人快跑后一般。
与此同时,面对病痛的侵袭和死神的威胁,先生则又常常表现出一种过人的淡定。实际上,对于自己的病情和发展下去的严重后果,他的心里比谁都清楚。去年11月,我在医院听先生谈起病况,他就表示,自己至多再能活一两年,这还是乐观的估计,少则只有几个月。对此,他又半开玩笑地说,自己的年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如较之活到八九十岁高寿者虽不算长,但与那些只活到六七十岁者相比也不算短了。他在遗嘱中还特地叮咛:“去世之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及追思会之类的仪式,生老病死乃是人生之常,不必特为渲染。”我想,先生的这一嘱咐,除了不愿身后给别人带来麻烦,留下悲伤,更为主要的还是源于他对生命本质的解悟,能以一种淡泊超然的心境对待死亡的来临。在他看来,人生来去本乃平常之事,有生就有死,死亡既然无法回避,那就应坦然去面对。
先生平素看上去虽略显严肃,但其实生性风趣,爱开玩笑,纵然在重病缠身的日子里,他依旧保持着这一个性和习惯。因为肿瘤的不断侵蚀和身体免疫力的下降,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先生经常发烧,反反复复。我却不止一次地听他打趣说,索性发烧发得再高一些,这样就可以杀死体内的癌细胞了。一句玩笑话,流露出的是先生洒然的内心。今年3月,我曾前往华山医院探视入院多日的先生,那时的他身体已相当虚弱,躺在病床上,有时连持续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但看上去精神还不错。其间,他以微弱却轻松的语调问:“最近学校里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我说了些自以为还比较有趣的事,先生听了,笑着说:“这些好像还不够有趣。”眉宇间充满了他惯有的喜欢打趣又略带几分顽皮的神情,仿佛不是在病榻上,而是像以往那样在茶餐桌上和朋友、学生一起笑谈戏语。
先生走了,同时带走的是他的劳累、他的病痛,还有一些事儿想做而来不及做的遗憾。但先生也留下了许多,包括他卓异的风范和杰出的业绩,尤其是他身罹癌病、面临死亡而对生命本质和价值的自我理解,这无疑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特别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