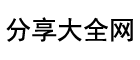赵振英的个人简介
赵振英,男,1917年生,黄埔军校14期学员,原国民革命军新六军14师40团第一营少校营长,1945年9月9日南京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会场警戒工作负责人。1950年考入南京大学。“文革”期间受尽折磨,1975年特赦。2010年9月,注册个人认证微博。
基本内容
赵振英, 出生于1917年,黄埔军校14期学员,1939年加入54军,1944年任中国驻印军第14师40团1营营长。
1945年9月9日,在南京的对日本 法西斯受降仪式中,他所在的第14师40团1营,作为受降仪式的警卫营,见证了受降仪式过程。
1945年9月9日早晨,受降地中央军校,大礼堂正门上,悬挂着中苏美英的国旗。正门上方的塔楼上嵌着一个巨大的红色“V”字以示胜利之意,下面悬着一块红布横幅,上面贴着“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会场”14个金字。
8时52分,悬挂在受降席和投降席上方的4个大型水银灯突然放光。时任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由礼台后方休息室走进来,全场迅速肃立,摄影记者纷纷拍照。
8时58分,由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引导日本投降代表、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及小林浅三郎等7人,自大礼堂正门步入会场。日军军官们都是低着脑袋、哭丧着脸,呆呆地任由中外记者拍照。受降席居中座的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左为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将张廷孟,右为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 萧毅肃。投降席上有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驻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茂三郎、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7人。参加受降仪式的中国方面,还有国民党将领 汤恩伯、王懋功、李明扬、郑洞国等。盟军将领有美军麦克鲁中将、柏德勒少将,英军海斯中将等。
9时04分,何应钦命冈村呈验签降代表证件。接着,何应钦将日本投降书中日文本各一份交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冈村用双手捧接,低头阅读。小林则在一旁替他磨墨。冈村阅毕,取笔蘸墨,写上自己的名字,并从上衣口袋内取出印章,盖于名下,低头俯视降书达50秒钟。 1945年9月9日9时07分。因为紧张,冈村的印章盖歪了,他面露难色,又无可奈何,只得让小林将他签名盖章的降书呈交何应钦。随后他立即起身肃立向何应钦深鞠一躬,骄横跋扈的日本侵略军在这一刻,终于无条件宣告投降。
9时10分,中国战区日本受降仪式完毕,日本代表退出会场。随后,何应钦向全国及全世界人士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南京受降仪式顺利完成。他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东亚及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亦从此进入到一个新纪元。”
老人开微博
赵老开微博,完全是无心插的柳。不过,在微博的世界里,很快就连绵成一片暖人心脾的树荫。
2010年9月8日,冰点周刊刊发了赵老的报道《老兵归来》,文章见报后,门户网站纷纷转载,跟帖众多。于是,周五下午,我与赵老约好前去拜访,一是给他老人家送报纸,二是找出网上的跟贴供他阅读,三是受友人之托,带东西给赵老。 到了赵老家,我在网上找出了相关报道和网友们的跟帖。老人家看得很高兴,哈哈笑着,合不拢嘴。然后,我又登录了我的微博,让他看看网友在我的博客后面的留言。赵老的情绪看上去很不错,他看着看着就问我一句:“这个微博是什么东西?”
我突然一激灵,“那么多人都在跟贴,向赵老致敬,为什么不给赵老注册一个微博呢?有了微博,这样的问候不是能更直接一些吗?”
于是,我向赵老详细地解释了微博的功能,然后征求了他的同意,为他注册了一个微博。
赵老多少还是有点犹豫,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习惯了做事谨小慎微,尤其是我在为他填职业的时候,写上“国民革命军新六军40团第一营少校营长”,他赶忙说:“这不好,这不好,这么写会出事吧?”
我听着心里一阵难受,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和他解释:“您是抗日的营长,是我们中国人的英雄,这是您的光荣。”
随后,我和一个在新浪微博的朋友通了个电话,告诉了他有这么件事儿,电话那头,听得出他也很激动。 后来,这个朋友告诉我,他在给赵老的微博加V的时候,“手都在抖”。我相信,这个发抖,不是其他什么原因,而是因为,他也是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微博注册好后,我就给赵老演示该如何操作,发了第一条微博:“大家好,我是赵振英。”但就在这个时候,让我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新浪朋友的推荐,从出现第一个粉丝开始,不到一分钟时间,赵老的粉丝就迅速增加了100多号人,向赵老问好和致敬的评论也接踵而至,速度快得我都看不过来。
我赶紧打开给他老人家看,赵老的眼神不太好,他只能带上老花镜,然后再拿上一个放大镜,一条一条认真地对着看,还时不时乐呵呵地问我一句:“他们真的是在和我说话吗?”
看着看着,赵老问我,这么多人关心我,我是不是也得说点什么啊,不然真过意不去。我说,那您就给大伙儿回上一条吧。
赵老是民国的高中毕业生,在当时可算是知识分子了。要知道,当年他离开国军后,报考了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东吴大学等五所重点大学,这五所大学可都给他发来了录取通知书的。而且,在抗日时,他是军部的参谋,可以用英语很流利地和美国人对话,汉语拼音对他来说,实在没什么难度。
只是,老人家刚刚学会上网,年龄大了,也看不清楚键盘,他只能用右手食指一个键盘一个键盘地按。在留言框里打出了:“我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恕不能一一回复。祝大家健康,生活幸福。”这么一行字,花了他将近五分钟时间。
在时隔65年后,日军南京投降仪式会场警戒工作负责人,93岁的前国军少校营长赵振英,终于堂堂正正,扬眉吐气地露脸了。
我把微博的详细操作程序,写在了一张纸上,让赵老背熟,他也托我转告博友们,以后每天会上网看看大家的问候,想起来了就写点东西。但他没有能力一条一条留言地回复,我也在这里代他向大家说声抱歉。
后来,我仔细想了想,一个93岁的远征军老兵开微博,在今天这个社会里,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公众来说,意味着赵老所代表的那段曾经被人为蒙蔽与误读的历史,终于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而且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这不仅要感谢像邓康延、晏欢这样的寻找者,也要感谢微博这样的新技术,在言论自由上的革命性进步。 而对于赵老来说,南京日军投降仪式,曾是中华民族的无上荣光,但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因为这个身份,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与侮辱,甚至一度以为这是段丑恶的历史,他的委屈与痛苦无处倾诉。今天,有这么多网友们向他表达尊敬之情,相信这多少能够抚慰一个暮年老人内心深处的伤口,也让他意识到,公道自在人心,他理应是这个民族亿万人景仰的英雄。
所以,希望朋友们能持续关注赵老。要知道,你们的每句问好,老人都用放大镜仔仔细细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过。我也代表赵老,谢谢各位了!
为抗日英雄找回荣耀
间昏暗狭小的房间,摆上一张双人床和一张书桌就难以转身了;书桌上镶在镜框里妻子微笑的遗像,深情地凝视着房间的主人。屋子里除了寂静还是寂静,只有偶尔从窗外传来几声邻近小学操场上孩童的嬉闹声。 房间的主人名叫赵振英,今年已经93岁了。老人满头白发,尽管拐杖在手,走起路来却依旧步履蹒跚。在过去的30多年里,他谨言慎行,就连看到街边戴红袖章的保安,都会感到些许恐惧。
在此前相当长的岁月里,连他的子女都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曾亲历过中国百年历史上最为荣耀的时刻,并在其中担任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礼堂举行。这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抵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胜利,在这个最重要的历史时刻里,时任国民党新六军14师40团第一营少校营长的赵振英,是投降签字仪式会场内外警戒工作的负责人。
这本该是少校个人历史上最为荣耀的一页。但在此之后,因为国民党军官身份,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判刑、坐牢,妻子被迫与他离婚。出狱后,老人一直蜗居在北京西郊的一处居民楼里,并决定永远将这个“秘密”烂在肚里。
然而无意之中,一幅来自异国他乡的老照片,以及一本写满签名的笔记本,打开了这个老兵尘封已久的记忆。深圳的一家民营纪录片公司闻讯而来,历时近两年,为老兵赵振英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名为《发现少校》。
“历史就像陈年的胶片,免不了尘埃和划痕,甚至断裂。”这家公司的老总邓康延说,“在时隔65年后,能够为本民族的英雄找回荣耀,这也是我们的荣幸。”
见证最光荣的时刻
1937年7月23日的那个下午,赵振英搭乘“七七事变”后的最后一列客车,离开了故乡北平城。
车上挤满了逃离北平的难民与学生。担心日军开火,车头上还挂了一面白旗。车过卢沟桥时行驶缓慢,赵振英甚至能看到,在远处的日军阵地上,有日军军官举着望远镜向列车观望。
铁路的这一边,是国民党第29军的阵地,中日两军处在对峙中,大战一触即发。满载着平民的客车从中间地带缓缓驶过,这个20岁的高中毕业生,心头突然涌起一阵“屈辱感”。
赵振英原本的理想,是想考入北京大学。但随着“七七事变”卢沟桥上的一声枪响,这个梦想被彻底击碎。从那一刻起,他和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汇聚到抗日救国的历史洪流中来,立志要将侵略者赶出中国。
在此后的8年里,这个年轻军官的战斗足迹遍布多个省份――湖南、四川、广东、云南。由于表现优异,他一路晋升,1944年4月,27岁的赵振英随中国远征军入印缅作战时,就已经是少校营长了。
尽管作战多年,但多半时间他都在军部担任参谋。在出任营长后,自己的部队又始终被作为预备队使用,很少有真正上战场作战的机会,作为一名军人,这成为他戎马生涯中不小的遗憾。
然而历史很快给了他一个万众瞩目的机会。
赵振英所在的国民党新六军,被称为国民党军队“王牌中的王牌”,军长廖耀湘,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1945年8月,抗战已接近尾声,蒋介石点名要求新六军进驻南京。他想用这支全副美式装备的威武之师,向投降的日本人展示中国的军威。
1945年8月28日,赵振英的第一营从湖南芷江飞往南京。从跳出机舱踏上南京土地的那一刻,赵振英与他的士兵们注定将被载入史册――这是在历经了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之后,第一支收复首都的中国军队。
随后,这个军衔为少校的营长又被上峰委派,负责1945年9月9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会场的警戒工作。在许多参战部队眼中,这个任务被视为“中国参战军人的最高荣耀”。
作为一名抗战史研究者,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的全过程,晏欢原本已经十分熟悉,但赵振英的描述,又为他补充了许多原本不为人知的细节。
投降签字仪式的地点,是在南京中央军校的大礼堂。从礼堂门口一直到外面的大街上,每隔50米,就竖着一根旗杆,用蓝白相间的布条包裹,旗杆上挂着同盟国中、美、英、法、苏的五面国旗。
每根旗杆下,都站着一个全副武装、精神抖擞的第一营士兵,他们身着绿色卡其布美式军装,戴着钢盔与白手套,背军用背包,手持美式冲锋枪。为了防止走火,士兵的枪膛里并没有上子弹。
签字仪式时,赵振英的位置在日本代表团投降席的左后方,他的士兵遍布整个会场,这些士兵的人数与站位,是赵振英在前一天就安排好的,并经过了再三演练。
在签字仪式的10多分钟里,会场里唯一能够自由走动的,就只有赵振英一个人。他的任务,是时刻注意部下的军姿,防止出现意外。
更让晏欢震惊的是,在他带去的当时美国记者拍下的受降仪式老照片中,赵振英甚至发现了一个疑似自己的身影。 这张老照片的主体部分,是中国受降席与日本投降席,但照片的左下角落,在一排士兵背后,站着一个面孔模糊的军官,身着马裤,脚蹬长筒马靴,腰间别着手枪,打扮与旁人明显不同。
“这个人有可能是我。”在赵振英的记忆中,作为会场警戒部队的最高长官,为了彰显军威,在受降仪式前些天,他特意到会场附近的裁缝铺里,订做了一套马裤制服。
而那张照片和签名本上的故事,赵振英也记得很清楚。
受降仪式后不久,1945年10月6日,在南京的新六军军官俱乐部开幕。新六军营级以上的军官,都出席了。那个时候,他们是众人仰慕的英雄与胜利者,在最上方那排军官的右侧,赵振英找到了自己微笑的面孔。
随后,新六军中的美军联络官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离开了中国。在走之前,约翰·葛顿南少校拿出了这个红色笔记本,让在场的中国军官在上面签名,作为对这段光荣岁月的纪念。
南京受降仪式,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显赫的一页。这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在抵抗外族侵略战争中取得胜利。这也成为赵振英一生中最为骄傲的经历。尽管时隔60多年,老人依旧记得当时的心情。
“略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兴奋!”老人的脸上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丝自豪感,“从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就没有打过胜仗,8年抗战,风餐露宿,终于把日本人打投降了!我能亲眼目睹这一切,荣耀啊!”
只是,当年那个年轻的少校营长不会想到,一度被他引以为傲的这分荣耀,很快变得黯淡无光。它先是被冲淡,然后被践踏,之后逐渐凋落,像落叶一样,被主人扫到内心深处最为隐秘的角落,一藏就是几十年。
少校变身工程师
在没有遇见晏欢之前,家人从来都不知道,赵振英有过这么荣耀的历史。
赵振英的儿子赵精一清楚地记得,2005年9月9日晚上,《新闻联播》播放了南京受降仪式60周年的新闻,电视机前原本沉默不语的老人突然开口说:“那个时候,我在现场。”
“老爷子不会是老糊涂了吧?”赵精一和媳妇打心眼儿里不相信,在他们心目中,沉默寡言的父亲,怎么会有如此光荣的历史?接下来,他们也没有追问父亲。
晏欢曾问过赵振英:“为什么你不告诉家里人呢?这多光荣啊?”
“我一直觉得这是臭史,是丑恶的历史。”老人的回答戳痛了晏欢,“你想想,要是不丑恶,后来为什么坐牢呢?好人能坐牢吗?”
在南京受降仪式后,赵振英只享受了短暂的两个月的平静生活。国共两党的内战一触即发,1946年初,新六军奉调北上,赵振英也随部队一起进入东北战区。
不过,这个少校营长已经厌倦了战争,他只想圆自己的大学梦。1947年,他参加了“留美军官考试”,并获得了沈阳考区的第二名。在赵振英的记忆中,日后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就是当年考上的幸运儿之一”。
但赵振英没有黄仁宇那么幸运――他最终落选,不得不返回部队。历史的大手,也把这支往昔的荣耀之师,推进了失败的深渊。1948年,新六军在辽宁黑山附近被解放军围歼,大部队被冲散,赵振英打扮成农民,趁乱脱离了战场。
随后,他一路南下,一直到杭州才停住了脚步。此时,已是1949年末。旧政权已被推翻,一个全新的政权,刚刚进入人们的视野。
赵振英在杭州租了一间民房,开始准备考试。因为高中打下的底子很好,他报考的5所大学,都寄来了录取通知书,最终,他选择了南京大学,成为工学院机械专业1950级的大学生,并在毕业之后,进入了一家国营工厂,成为一名工程师。 从士兵口中的“赵营长”,变成工人口中的“赵工”,赵振英一度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告别颠沛流离,开始平静的生活。
可他错了。
从“罪人”回归常人
1966年,“文革”开始,人们在赵振英的档案中查到了他的历史,从那时起,赵振英便陷入了一场长达10年的噩梦中。
每天早上,他上班之前,都要去工厂的传达室领上一块“反革命分子赵振英”的牌子,并把它挂在脖子上,下班后再交回去。革命群众随时都会对他发动批斗,他弯腰90度站在人群中,戴着红袖章的革命群众围着他,用木棍肆意殴打。
担心被人抄家,在一个深夜,这个工程师含泪烧掉了他的过往。那些战场上的照片、徽章、以及能够证明自己军官身份的文件,随着一阵火光,化为灰烬。
3年后的一天,两个警察出现在他面前,他们让赵振英在一份逮捕书上签了字,给他戴上手铐,将他带到了一个体育场里。这儿正在举行一场公判大会,在革命群众震耳欲聋的“打倒”声中,赵振英以“国民党反动军官”的罪名,被判了20年有期徒刑。
监狱里的日子是难熬的。一张大通铺,睡着10多个人,经常吃不饱。赵振英的活儿,是在一个烧砖的窑厂里,清理烧剩下的灰尘与碎砖。每天,他都要推着三轮车,在几十个窑洞里来回走,一天下来,全身覆满灰尘,只露出两只眼睛。
然而精神上的折磨,远远超过身体上的折磨。对于自己的罪名,赵振英始终“不服气”,他一边劳改,一边给法院写申诉书,经常处于恍惚之中。有天晚上收工回来洗脚,他没有脱鞋子,就把脚伸进了盆里。
寄出的十几封申诉书,如泥牛如海,一去无回,等来的,却是一纸离婚判决书。
赵振英的妻子宋玉岐,是1946年他在长春驻守时认识的。她出生于一个大户人家,还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女大学生。从哈尔滨医科大学口腔医学系毕业后,她成为吉林铁路医院的一名牙科医生,赵振英去那儿看牙,两人由此结识、相爱,并于一年后结婚。
夫妻俩的感情一直很好。赵振英心里清楚,妻子一定是不得已才作出这样的决定。果然,过了几天,儿子赵精一来探监,偷偷告诉父亲:“我妈让你放心,她不会和别的男人结婚的。”
事后,赵振英获知,妻子为了他受了许多苦。在那个时代,“反革命分子”的家属是抬不起头的,原本娇生惯养的妻子,被下放到河南劳动,白天打扫卫生,晚上挨批斗,批斗完了还不能回家,只能睡在写大字报的台子上,天气冷了,就用大字报盖在身上御寒。
1975年,这场噩梦总算终结。当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官的特赦令,赵振英也在这个行列中。特赦后的第二天,赵振英便让单位开了封介绍信,与妻子复婚。
在这之后的20年中,这对历经磨难的夫妻,终于回归了平静的生活。
在赵振英的孙子赵悦眼中,“爷爷奶奶的感情好到不可思议”。从小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赵悦几乎没见过老两口吵过架。记忆中唯一的一次,是奶奶想让爷爷多吃一块馅饼,爷爷不愿吃,“奶奶气得好几个小时没理他。”
赵振英和妻子在阳台上养了许多花――君子兰、月季、海棠……这个从小就在城市里长大的女人,很喜欢看花,在赵振英身体尚好的那些年里,每到春天,他就骑着三轮车,载着妻子,到附近的玉渊潭公园,手挽着手,在樱花树下一走就是大半天。
不过,在2005年后,赵振英就再也没去过那个公园。
这年的12月18日,宋玉岐去世。临走的前一天,家人还听到,病床上昏迷的老人家,突然迷迷糊糊地说:“老赵,剩菜剩饭要烫烫啊,每天记得要烧两壶开水。”
妻子去世后,赵振英没有将妻子的骨灰埋掉,而是将骨灰盒保存在卧室里,就好像老伴依然陪着他一样。他的愿望,是希望在他自己走后,家人把他和妻子两人的骨灰混在一起,装进罐子里,丢进大海。
直到今天,这位老兵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妻子的遗像前,和她说上几句话。这个习惯,他已经保持了将近5年。
“我知道你在苦苦等着我,我也在每天怀念你,我们就快些到一起去吧。”老人哽咽着,眼角泛出隐约的泪花,“我不愿意留在这个大地上。怎么说呢?这个大地,对我实在是……太苛刻了……”
他旁边的镜框里,是妻子宋玉岐的遗像。这个慈祥的老妇人,一直深情地凝视着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