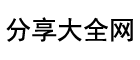三毛的故事是真的吗
三毛的故事是真的。
三毛,原名陈懋(mào)平(后改名为陈平),中国现代作家,1943年出生于重庆,1948年,随父母迁居台湾。1967年赴西班牙留学,后去德国、美国等。1973年定居西属撒哈拉沙漠和荷西结婚。1981年回台后,曾在文化大学任教,1984年辞去教职,而以写作、演讲为重心。1991年1月4日在医院去世,年仅四十八岁。
生平经历:该目录内容以陈平为第一人称。
1、早年
陈平三毛祖籍浙江省定海,据陈平家谱《陈氏永春堂宗谱》记载陈平祖上早期从河南迁往浙江。父陈嗣庆是成功的律师、母缪进兰,陈平1943年出生于重庆,排行第二,有一个姐姐陈田心与二个弟弟陈圣、陈杰。姐姐陈田心比三毛大3岁。抗日战争胜利后跟着父母搬到南京,再迁到台北。陈平在台北入读中正国民小学,1954年考入台湾省立台北第一女子中学。小时就喜欢捡拾别人丢弃的物品把玩,自得其乐。
2、初中休学
1955年陈平初二的时候,数学常得零分。至第二学期陈平发现,数学老师每次小考都是课本后面的习题。为了不要留级,陈平把题目背下来,小考一连考了六个一百分。数学老师开始怀疑她作弊。陈平对老师说:“作弊,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就算你是老师,也不能这样侮辱我。”于是数学老师高于所学难度的题目叫陈平作答,得到零分后,老师当着全班的同学用毛笔在她的眼睛周围画了两个代表零蛋的大圈并用语言羞辱陈平。在第二天上学前系鞋带时想到此事晕倒,心理出现极大障碍,此后更是频频晕倒,于是经常逃学到公墓看小说,最后终于休学。1956年一度复学,仍经常逃学到图书馆看书,后正式退学。刚休学时,陈平被父母转进台北美国学校,被送去学插花、钢琴、国画,和名家黄君璧习山水,向邵幼轩习花鸟。她喜欢看书,她父亲就教她背唐诗宋词,看《古文观止》,读英文小说,但是陈平经此打击,患上忧郁症,一直处于自我封闭的心态。曾割腕自杀,也曾看过心理医生,但一周一次的心理治疗并无帮助。
3、学画
陈平关在家中一段时间。姐姐陈田心的朋友陈骕在随顾福生学画油画。陈平非常羡慕,于是也随顾福生习画。多年之后陈平回忆初见顾福生的情景:
“许多年过去了,半生流逝之后,才敢讲出:初见恩师的第一次,那份‘惊心’,是手里提着的一大堆东西都会哗啦啦
掉下地的‘动魄’。如果,如果人生有什么叫做一见钟情,那一霎间,的确经历过。”—— 三毛 《我的快乐天堂》
一开始顾福生教陈平素描与水彩画,是当时除了父母外,唯一与陈平沟通的人。后顾福生因要出国介绍韩湘宁为陈平学画的老师,后来韩湘宁也因要出国又介绍了彭万墀。
4、文学启蒙
顾福生不是教育家,却鼓励陈平在文学的领域发展,帮助她找到自己的方向。除了引介《笔汇》与《现代文学》杂志,并将波特莱尔、左拉、卡缪、陈映真等作家的作品介绍给陈平,开启她对当时台湾文坛的认识。顾福生并将一篇陈平的文章转交他的好友《现代文学》杂志主编白先勇,从此打开陈平自我封闭的心态,改变了陈平的一生[参 1]。
1962年12月,署名陈平的文章《惑》经顾福生推荐在白先勇主编的《现代文学》杂志第十五期发表,给陈平带来极大的鼓励。白先勇后来回忆《惑》是一则人鬼恋的故事,的确很奇特,处处透著不平常的感性,小说里提到《珍妮的画像》,那时台北正映了
入文化学院这部电影不久,是一部好莱坞式十分浪漫离奇人鬼恋的片子,这大概给了三毛灵感[参 1]。”之后陈平开始在报章杂志投稿,1963年在《皇冠杂志》十九卷第六期发表《月河》。
陈平很仰慕白先勇的同学陈秀美,顾福生亦介绍陈秀美作陈平的朋友,鼓励陈平走出自我封闭的生活。陈秀美觉得当时三毛很自恋。陈秀美并曾以三毛为原型,写了一篇小说《乔琪》。1964年陈秀美鼓励陈平去向文化学院董事长张其昀请求入学文化学院作没有学籍的选读生。结果获张其昀特许,至该院哲学系当选读生,没有高中学历的陈平成绩优异。
陈平曾对当时的作品《雨季不再来》一书作出以下的评论“《雨季不再来》还是一个水仙自恋的我。我过去的东西都是自恋的。如果一个人永远自恋那就完了。……很多人可以看到我过去是怎样的一个病态女孩。”文化学院教授胡品清亦在《皇冠》与《联合报副刊》分别发表了写给Echo的书简。“胡对她的印象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拔俗的、谈吐超现实的、奇怪的女孩,像一个谜。1967年她出国后一个月,胡的《断片三则》之一描写她:喜欢追求幻影,创造悲剧美,等到幻影变为真实的时候,便开始逃避。”
5、初恋
在文化学院时,陈平仰慕同校已以舒凡为笔名出版两本书的才子梁光明,主动给出联系方式,两人之后开始交往。梁光明升上大四时,大三的陈平多次逼婚不成便已去西班牙留学作为筹码,结果陈平办妥出国手续反而造成两人分手。陈平因此自杀缝了28针。
6、游学经历
1967年赴西班牙留学,先学
西班牙文,半年后入马德里文哲学院。在西班牙时遇到还在读高三的荷西·马利安·葛罗。后就读于德国西柏林哥德书院得到德文教师证书,又到美国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 ,本想专攻陶瓷后来在法律图书馆打工。留学期间不时把握机会打工赚钱,当过西班牙马略卡岛导游、德国商店香水模特、美国图书馆员等,游历过东德、波兰、南斯拉夫、捷克、丹麦等国。在这期间她也交了几位男朋友。在西班牙时,有一日本籍的富商同学;在德国时有一名后来成为外交官的德国同学;在美国时,有一名台湾籍的留美博士。还曾在柏林墙与一位军官有过浪漫的邂逅,但都无果。
7、返国与情伤
1971年返国,应张其昀之聘,在中国文化学院德文系、哲学系任教,也在政工干校与实践家专教课。70年代,台湾明星咖啡屋风华正茂,有说法称此期间陈平在“明星”咖啡厅结识一位画家邓国川,因非常喜欢对方的作品而答应了画家的求婚,遭到家人集体反对,陈平不顾众多反对之声坚决要与画家结婚,即将举行婚礼前,却发现了对方是有妇之夫。同年,喜欢运动的陈父鼓励女儿与他一起打网球,在网球场上他们认识了一位年龄较长的德国教师,后来陈平与之相识,相爱,一年后,陈平答应了德国教师的求婚,有一天他们一起去订制结婚的名片,结果当天晚上,德国教师却心脏病突发猝死,之后陈平伤心欲绝,服安眠药自杀,但被救回。17年后,三毛回忆此事,“那盒名片直到今天还没有去拿。”
8、与荷西结婚
陈平与荷西1972年陈平遇到上述情感上和婚姻上的打击,再度远走西班牙。与六年前遇到的西班牙人荷西·马利安·葛罗重逢。当时尚是高中生的荷西此时已大学毕业,服完兵役,也有了潜水师执照。原本荷西计划与一群朋友一同乘帆船去希腊地中海一带潜水旅游,邀请陈平担任厨师同行,但陈平对撒哈拉沙漠情有独锺。后来荷西没有去乘帆船,却在西属撒哈拉磷矿厂找到工作。1974年,陈平在非洲沙漠小镇(西属撒哈拉的阿尤恩)与荷西结婚,开始两人在西属撒哈拉的婚姻生活。荷西送给陈平的结婚礼物是他花了一番功夫在沙漠中找到的一副完整的骆驼头骨。陈平非常喜欢这份结婚礼物,以后一直保存著。
9、成名撒哈拉
1972年陈平陈平与荷西遇到上述情感上婚姻上的打击,再度远走西班牙。与六年前遇到的西班牙人荷西·马利安·葛罗重逢。当时作为背景描写自己异国婚姻的作品与当时副刊上其他文章截然不同,吸引大批读者。历经两度情感上的打击,三毛的作品此时已超越以往自恋的纯文学风格,虽然只是描写生活的散文,但显得乐观开朗又有趣。此后她充满异国风情的作品源源不断在《联合报副刊》刊出,后集结出版《撒哈拉的故事》、《稻草人手记》和《哭泣的骆驼》等书。这一系列的书大受全世界华人社群读者欢迎,历久不衰。
10、丧夫
1975年11月,摩洛哥组织绿色进军,35万名志愿者开进西属撒哈拉。 1976年2月西班牙撤离西属撒哈拉。三毛与荷西最后也离开西属撒哈拉,前往西班牙属地加那利群岛。荷西与三毛后来住在加那利群岛中的丹娜丽芙岛。1979年9月30日,当天正好是中秋节,荷西在三毛父母往访期间在拉帕尔马岛的海中潜水时意外丧生。三毛历经第三度情感上的打击,姐姐陈田心回忆三毛亲自用手去挖荷西的坟墓,认为如果不是父母在,她一定跟着荷西走了[参 5]。三毛在双亲扶持下飞返台湾暂住,稍后又回到加纳利群岛,一直无法走出伤痛。
11、游记
1981年11月,由台北《联合报》特别赞助前往中、南美洲十二国旅行半载,撰写所见所闻。1982年5月,飞返台北,作“三毛女士中南美纪行演讲会”环岛演讲,主讲“远方的故事”,出版《万水千山走遍》。
1982年任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讲授“小说创作”、“散文习作”,深受学生喜爱。1984年因健康关系辞卸教职,前往美国接受割治子宫癌手术,以写作、演讲维生。1984年5月,皇冠杂志社举办了一次“阴间之旅”活动,由吕金虎施法及带领三毛进地府一游。1985年一度丧失记忆,神经错乱。1987年3月,出版有声书《三毛说书》;7月,出版有声书《流星雨》(童话故事)。
12、逝世
1991年1月4日,因子宫内膜增生症住院治疗的三毛被发现在台北荣总病房内逝世,死因为以丝袜自缢而亡。有种说法是,三毛处于“精神耗弱”的状态,临睡前不服用安眠药无法入睡,安眠药剂量不断增加下,最终因服用剂量过重,不慎迷糊中被丝袜缠住颈部而窒息逝世,终年48岁。她的家人也澄清她不是自杀。她去世前半个月,还曾告诉母亲,她想做修女。另一方面,各种流言绘声绘影,说三毛的早逝是她热衷通灵造成的。外界也流传她是被谋杀的言论,作家张景然更在他的著作《哭泣的百合:三毛死于谋杀》中对此一说进行了一连串论证,在这之前给王洛宾写过绝笔书。
三毛得情感经历…
三毛一生中多次恋爱。19岁入台北华冈文化大学选读生。人生第一次恋情是跟文化大学戏剧系高三毛一届的梁光明,梁光明现在是台湾作家,笔名舒凡。三毛和梁光明相恋三年。梁光明毕业前三毛设想着跟梁光明结婚,而梁光明却想先立事业后结婚。两人在婚姻问题上的纠葛让爱情变成累赘,三毛开始逼婚,梁光明如果不跟她现在结婚,她就马上去西班牙。结果梁光明选择了不结婚。大学未毕业的三毛痛苦地选择去西班牙。 到了西班牙,三毛进了马德里大学文哲学院。恋上西班牙人荷西,当时荷西只18岁,而三毛已经24岁。三毛在自己的作品中谈到了第一次见荷西的感觉:“我第一次看见他时,触电了一般,心想,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英俊的男孩子?如果有一天可以做为他的妻子,在虚荣心,也该是一种满足了。”热恋过后,荷西向三毛求婚,他让三毛等他六年,四年大学和两年的兵役,六年后,荷西说他会娶三毛。三毛觉得六年太漫长,到时自己是30岁的大龄女青年。理智地选择了离开。很快三毛跟好几个国家的留学生恋爱。其中有家里开豪华餐厅的日本留学生。 再后来,三毛为了自己的德国籍男友离开西班牙去往德国柏林,进入歌德学院。德国男友为了自己的外交官梦一心扑在学习上,每天超过16个小时在学习。睡觉的时候也小声地用收音机播放学习材料。他用自己的方式深爱着三毛。生性浪漫的三毛忍受不了,最终选择离开,前往美国伊利诺斯大学。伊利诺斯大学一位化学博士掳获了三毛的心,这位博士还是三毛堂哥的同学。“每天中午休息时间,总是堂哥的好同学,准时送来一个纸口袋,里面放着一块丰富的三明治,一只白水煮蛋、一枚水果。”可这段爱情最终没有结出果实。三毛选择了回台湾。此时,三毛27岁。 回到台湾,三毛又有了新恋情,可惜遇人不淑,即将结婚前三毛才发现对方是位有妇之夫。痛心之后三毛很快跟一个台北某大学40多岁的德国籍教授建立恋爱关系并且接受了对方的求婚。可惜命运捉弄人,结婚前夕,新郎心脏病发猝死。台北成了三毛的伤心地,不久三毛离开台北去往熟悉的西班牙,跟已经长得健硕成熟的荷西重逢,并且成为荷西的新娘,结婚的地点在撒哈拉沙漠。结婚六年后,潜水专家荷西在潜水时不幸去世。这一年,荷西30岁,三毛36岁。12年后,写完《滚滚红尘》后,三毛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用丝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与荷西在撒哈拉生活的日子是三毛此生最幸福的时光。两人 1973年在西属撒哈拉登记结婚。1976年,三毛的第一部作品《撒哈拉的故事》面世。三毛最重要的作品讲的全部是在撒哈拉的日子。写的大部分是跟荷西在一起的生活琐碎,以及多民族之间的趣闻。作家三毛,更确切地说,她只是用笔在记录自己的人生。像在自己给自己写传记。只是这本传记充满了孤独,伤痕,漂泊,沙漠。也有爱情。 写梦里花落知多少时荷西已不在了,应该是为了纪念荷西
舒凡还活着么?我说的是和三毛有过一段感情故事的那个人。
还活着 。
说说他的经历:
三毛选择用自杀的方式告别,我们只是感觉痛惜,并没有太多惊讶,因为这是她习惯的方式。早在1964年,21岁的她初恋失败,就曾自杀过。
小时候的三毛身体瘦弱,性格独立、执拗、不合群,在父母眼中,三毛是个极端敏感和神经质的人。19岁时,三毛做了台湾文化学院哲学系的一名选读生。在家休学七年后,她还是走回了菁菁校园。
在学校,三毛注意到几乎所有的女生都会称赞一个叫舒凡的男生。舒凡,本名梁光明,戏剧系二年级的学生,但是已经出版了两本集子,是学院大名鼎鼎的才子。三毛于是借了他的书来读,书写得很漂亮,三毛读毕便爱上了他。在此后的三四个月裏,三毛成了舒凡的尾巴,舒凡出现在哪,她就会出现在哪。
终于有一天,三毛在操场偶遇了舒凡。三毛想:一切总得有个开始吧,成长这本书总得靠自己动手翻。于是,三毛走向舒凡,抽出他衬衣口袋裏的钢笔,掰开舒凡的手掌,然后飞快地将家中的电话号码写在他的手掌上。写完,三毛转身跑掉了。她一口气冲回教室,气喘吁吁地收拾著自己的书本。她不要上课了,她要回家等舒凡的电话。
三毛的痴情终于打动了冷傲的舒凡。第一次约会,舒凡看著面前这个仰著脸的女孩,她不漂亮,可是她有一双闪动著生命力的眼睛。初恋就这样开始了。两个人,一起读书,一起吃饭,一起逛街……
但初恋的人通常都是脆弱的,何况三毛又是那种一旦付出就绝不肯为自己留后路的痴情者呢?在他们相恋的日子裏,三毛常为了两人之间的一些小事而生气。有时是因为舒凡不牵她的手,不拥她的腰,有时是因为舒凡不陪她共用午餐而一个人去睡午觉……这些让舒凡不胜其烦。在舒凡即将毕业的时候,三毛提出了一个在舒凡看来异常荒谬的要求:结婚。最后,舒凡只有疲倦而冷漠地对三毛说:“我们不要再相互折磨了,我太累了。”就像一个水晶器皿落地的声音,在三毛心裏,有什麼东西,碎了。
三毛初恋
雨季不再来
这已不知是第几日了,我总在落著雨的早晨醒来,窗坍照例是一片灰镑镑的天
空,没有黎明时的曙光,没有风,没有鸟叫。后院的小树都很寥寂的静立在雨中,
无论从那一个窗口望出去,总有雨水在冲流著。除了雨水之外,听不见其他的声音
,在这时分里,一切全是静止的。
我胡乱的穿著衣服,想到今日的考试,想到心中挂念著的培,心情就又无端的
沉落下去,而对这样的季候也无心再去咒诅它了。
昨晚房中的台灯坏了,就以此为藉口,故意早早睡去,连笔记都不想碰一下,
更不要说那一本本原文书了。当时客厅的电视正在上演著西部片,黑暗中,我躺在
床上,偶尔会有音乐、对白和枪声传来,觉得有一丝朦胧的快乐。在那时考试就变
得极不重要,觉得那是不会有的事,明天也是不会来的。我将永远躺在这黑暗里,
而培明日会不会去找我也不是问题了。不过是这个季节在烦恼著我们,明白就会好
了,我们岂是真的就此分开了,这不过是雨在冲乱著我们的心绪罢了。
每次早晨醒来的时候,我总喜欢仔细的去看看自己,浴室镜子里的我是一个陌
生人,那是个奇异的时分。我的心境在刚刚醒来的时候是不设防的,镜中的自己也
是不设防的,我喜欢一面将手浸在水里,一面凝望著自己,奇怪的轻声叫著我的名
字━━今日镜中的不是我,那是个满面渴想著培的女孩。我凝望著自己,追念著培
的眼睛━━我常常不能抗拒的驻留在那时分里,直到我听见母亲或弟弟在另一间浴
室里漱洗的水声,那时我会突然记起自己该进入的日子和秩序,我就会快快的去喝
一杯蜂蜜水,然后夹著些凌乱的笔记书本出门。
今早要出去的时候,我找不到可穿的鞋子,我的鞋因为在雨地中不好好走路的
缘故,已经全都湿光了,于是我只好去穿一双咖啡色的凉鞋。这件小事使得我在出
门时不及想像的沉落,这凉鞋踏在清晨水湿的街道上的确是愉快的。我坐了三轮车
去车站,天空仍灰得分不出时辰来。车帘外的一切被雨弄得静悄悄的,看不出什么
显然的朝气,几个小男孩在水沟里放纸船,一个拾拉圾的老人无精打采的站在人行
道边,一街的人车在这灰暗的城市中无声的奔流著。我看著这些景象,心中无端的
升起一层疲惫来,这是怎么样令人丧气的一个日子啊。
下车付车钱时我弄掉了笔记,当我俯身在泥泞中去拾起它时,心中就乍然的软
弱无力起来。培不会在车站吧,他不会在那儿等我,这已不知是第几日了,我们各
自上学放学,都固执的不肯去迁就对方。几日的分离,我已不能清楚的去记忆他的
形貌了,我的恋念和往日他给我的重大回忆,只有使得我一再激动的去怀想他,雨
中的日子总是湿的,不知是雨还是自己,总在弄湿这个流光。今日的我是如此的撑
不住,渴望在等车的时候能找到一个随便什么系的人来乱聊一下,排队的同学中有
许多认识的,他们只抬起头来朝我心事重重的笑了笑,便又埋头在笔记簿里去,看
样子这场期终考试弄得谁都潇洒不起来了。我站在队尾,没有什么事好做,每一次
清晨的盼望总是在落空,我觉著一丝被人遗忘的难受,心中从来没有被如此鞭笞过
,培不在这儿,什么都不再光彩了。站内的日光灯全部亮著,惨白的灯光照著一群
群来往的乘客,空气中弥漫著香烟与湿胶鞋的气味,扩音器在播放著新闻,站牌的
灯一亮一熄的彼此交替著,我呼吸著这不湿的空气,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厌倦而又无
奈的日子。
想到三个多月前的那日,心情就无端的陷入一种玄想中去,那时正是注册的日
子,上一个学期刚从冬季寒冷的气候中结束,我们放假十天就要开始另一个新的学
期。那天我办完了注册手续才早晨十点多点,我坐在面对著足球场的石砌台阶上,
看著舞专的学生们穿了好看的紧身舞衣在球场上跳舞,那时候再过几日就是校庆了
,我身后正有一个老校工爬在梯子上漆黄色的窗框,而进行曲被一次次大声的播放
著,那些跳舞的同学就反复的在练习。当时,空气中充满著快乐的音乐和油漆味,
群山在四周低低的围绕著。放眼望去,碧空如洗,阳光在缓缓流过。我独自坐在那
儿,面对著这情景,觉得真像一个活泼安适的假日,我就认真的快乐起来。那份没
有来由的快乐竟是非常的震撼著我。后来开学了,我们半专心半不专心的念著书,
有时逃课去爬山,有时在图书馆里发神经查生字,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接著雨就来
了,直到现在它没有停过。我们起初是异常欢悦的在迎接著雨,数日之后显得有些
苦恼,后来就开始咒诅它,直到现在,我们已忘了在阳光下上学该是怎么回事了。
从车站下车到学校大约有二十分钟的路,我走进校园时人已是透湿的了,我没有用
雨具的习惯,每天总是如此的来去著。我们教室在五楼天台的角上,是个多风的地
方。教室中只有几个同学已经先到了,我进门,摊开笔记,靠在椅子上发愣,今日
培会来找我么?他知道我在这儿,他知道我们彼此想念著。培,你这样不来看我,
我什么都做不出来,培,是否该我去找你呢,培,你不会来了,你不会来了,你看
,我日日在等待中度日━━四周的窗杠开著,雨做了重重的帘子,那么灰重的掩压
了世界,我们如此渴望著想看一看帘外的晴空,它总冷漠的不肯理睬我们的盼望。
而一个个希望是如此无助的被否定掉了,除了无止境的等待之外,你发现没有什么
其他的办法再见阳光。
李日和常彦一起走进来,那时已是快考试了,李日是个一进教室就喜欢找人吹
牛的家伙。他照例慢慢的踱进来,手中除了一枝原子笔之外什么也没带。
“卡帕,你怎么穿这种怪鞋子?”卡帕是日本作家芥川的小说《河童》的发音
,在雨季开始时我就被叫成这个名字了。
“没鞋了,无论皮鞋球鞋全湿了,不对么?”
“带子太少。远看吓了我一跳,以为你干脆打赤足来上学了。”李日一面看著
我的鞋,一面又做出一副夸张的怪脸来。
“我喜欢这种式样,这是一双快乐的鞋子。”
“在这种他妈的天气下你还能谈快乐?”
“我不知道快不快乐,李日,不要问我。”
“傻子,李日怕你考试紧张,跟你乱扯的。”常彦在一旁说。
“不紧张,不愉快倒是真的,每次考试就像是一种屈辱,你说你会了,别人不
相信,偏拿张白纸要你来证明。”我说著说著人就激动起来。
“卡怕,有那么严重么?”常彦很费思索的注视著我。
“他妈的,我乱说的,才不严重。”说著粗话我自己就先笑起来了。
这是一种没有来由的倦怠,你如何向人去解释这个时分的心情呢,今晨培也没
有来找,而日复一日的等待就只有使得自己更沉落下去。今晨的我就是如此的撑不
住了,我生活在一种对大小事情都过分执著的谬误中,因此我无法在其中得著慰藉
和亮光了。好在这心情已非一日,那是被连串空泛的琐事堆积在心底的一个沙丘,
禁不住连日的雨水一冲,便在心里乱七八糟的奔流起来。
这是一场不难的考试,我们只消对几个哲学学派提出一些评论,再写些自己的
见解,写两千字左右就可通过。事实上回答这些问题仍旧是我很喜欢的一件工作,
想不出刚才为什么要那么有意无意的牵挂著它。仔细的答完了卷子,看看四周的同
学,李日正拉著身旁埋头疾书的常彦想要商量,常彦小声说了一点,李日就马上脸
色发光的下笔如飞起来,我在一旁看了不禁失笑,李日的快乐一向是来得极容易的
。此时的我心中想念著培,心中浮出一些失望后的怅然,四周除了雨声之外再听不
出什么声音来。我合上了卷子,将脚放在前面同学的椅子上轻轻的摇晃著,那个年
轻的讲师踱过来。
“是不是做完了?做完就交吧。”
“这种题目做不完的,不过字数倒够了。”
他听了笑起来,慢慢的踱开去。
我想不出要做什么,我永远学不会如何去重复审视自己的卷子,对这件事我没
有一分钟的耐心。雨落得异常的无聊,我便在考卷后面乱涂著━━森林中的柯莱蒂
(注),雨中的柯莱蒂,你的太阳在那里━━那样涂著并没有多大意思,我知道,
我只是在拖延时间,盼望著教室门口有培的身影来接我,就如以前千百次一样。十
五分钟过去了,我交了卷子去站在外面的天台上,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整天都没
课了,我们已在考期终考了。整幢的大楼被罩在雨中,无边的空虚交错的撑架在四
周,对面雨中的宿舍全开著窗,平日那些专喜欢向女孩们呼叫戏谑的男孩们一个也
不见,只有工程中没有被拆掉的竹架子在一个个无声的窗口竖立著。雨下了千万年
,我再想不起那些经历过的万里晴空,想不起我干燥清洁的鞋子,想不起我如何用
快乐的步子踏在阳光上行走。夏季没有带著阳光来临,却带给我们如许难捱的一个
季候。教室内陆续有人在交卷,那讲师踱出来了。他站著看了一会雨。
“考完了就可以回去了,我们这门课算结束了。在等谁吗?”
“没有,就回去了。”我轻轻的回答了一声,站在雨中思索著。我等待你也不
是一日了,培,我等了有多久了,请告诉我,我们为什么会为了一点小事就分开了
,我总等著你来接我一块下山回去。
这时我看见李日和维欣一起出来。维欣是前一星期才回校来的,极度神经衰弱
,维欣回乡去了快一个月。
“考得怎么样?”我问维欣,平日维欣住在台北姑母家中,有时我们会一起下
山。
“六十分总有的,大概没问题。”维欣是个忧郁的孩子,年龄比我们小,样子
却始终是落落寡欢的。
“卡帕,你准是在等那个戏剧系的小子,要不然甘心站在雨里面发神经。”李
日一面跳水塘一面在喊著。
“你不许叫他小子。”
“好,叫导演,喂,培导演,卡帕在想你。”李日大喊起来。我慌了。
“李日,你不要乱来。”维欣大笑著拉他。
“卡帕,你站在教室外面淋雨,我看了奇怪得不得了,差一点写不出来。”李
日是最喜欢说话的家伙。
“算了,你写不出来,你一看常彦的就写出来了。”
“冤枉,我发誓我自己也念了书的。”李日又可爱又生气的脸嚷成一团了,这
个人永远不知忧愁是什么。
这时维欣在凝望著雨沉默著。
“维欣,你暑假做什么,又不当兵。”我问他。
“我回乡去。”
“转系吧,不要念这门了,你身体不好。”
“卡帕,我实在什么系都不要念,我只想回乡去守著我的果园,自由自在的做
个乡下人。”
“书本原来是多余的。”
“算了,算了,维欣,算你倒楣,谁要你是长子,你那老头啊━━总以为送你
念大学是对得起祖宗,结果你偏闷出病来了。”李日在一旁乱说乱说的,维欣始终
性情很好的看著他,眼光中却浮出一层奇怪的神情来。
我踏了一脚水去洒李日,阻止他说下一句,此时维欣已悄悄的往楼梯口走去,
李日还毫不觉得的在踏水塘。
“维欣,等等我们。李日,快点,你知道他身体不好,偏要去激他。”我悄悄
的拉著李日跟在维欣身后下去。
下楼梯时我知道今日我又碰不著培了,我正在一步一步下楼,我正经过你教室
的门口,培,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是这样的想念著你,培,我们不要再闹了,既
然我们那么爱著,为什么在这样近在眼前的环境中都不见面。
李日下楼时在唱著歌。
“我知道有一条叫做日光的大道,你在那儿叫著我的小名呵,妈妈,我在向你
赶去,我正走在十里外的麦田上……”
“喂,卡帕,这歌是不是那戏剧系的小子编出来的?告诉他,李日爱极了。”
这儿没有麦田,没有阳光,没有快乐的流浪,我们正走在雨湿的季节里,我们也从
来没有边唱著歌,边向一个快乐的地方赶去,我们从来没有过,尤其在最近的一段
时分里,快乐一直离我们很远。
到楼下了,雨中的校园显得很寥落,我们一块儿站在门口,望著雨水出神,这
时李日也不闹了,像傻子似的呆望著雨。它又比早晨上山时大多了。
“这不是那温暖的雨。”维欣慢慢的说。
“等待阳光吧,除了等待之外怎么发愁都是无用的。”我回头对他鼓励的笑了
笑,自己却笑得要落泪。
“算了,别等什么了,我们一块儿跑到雨里去,要拚命跑到车站,卡帕,你来
不来。”李日说著人就要跑出去了。
“我们不跑,要就走过去,要走得很泰然的回去,就像没有下雨这等事一样。
”
“走就走,卡帕,有时你太认真了,你是不是认为在大雨里跑著就算被雨击倒
了,傻子。”
“我已没有多少尊严了,给我一点小小的骄傲吧。”
“卡帕,你暑假做什么?”维欣在问我。
“我不知道,别想它吧,那日子不来,我永远无法对它做出什么恳切的设想来
,我真不知道。”
历年来暑假都是连著阳光的,你如何能够面对著这大雨去思想一个假期,虽然
它下星期就要来临了,我觉得一丝茫然。风来了,雨打进门檐下,我的头发和两肩
又开始承受了新来的雨水,地上流过来的水弄温了凉鞋,脚下升起了一阵缓缓的凉
意。水聚在我脚下,落在我身上,这是六月的雨,一样寒冷得有若早春。
雨下了那么多日,它没有弄湿过我,是我心底在雨季,我自己弄湿了自己。
“我们走吧,等什么呢。”维欣在催了。
“不等什么,我们走吧。”
我,李日,维欣,在这初夏的早晨,慢慢走进雨中,我再度完全开放的将自己
交给雨水,没有东西能够拦阻它们。雨点很重的落在我全身每一个地方,我已没有
别的意识,只知道这是雨,这是雨,我正走在它里面。我们并排走著,到了小树那
儿它就下得更大了,维欣始终低著头,一无抗拒的任著雨水击打著。李日口中含了
一支不知是否燃著的新乐园,每走一步就挥著双手赶雨,口中含糊而起劲的骂著,
他妈的,他妈的,那样子看不出是对雨的欢呼还是咒诅。我们好似走了好久,我好
似有生以来就如此长久的在大雨中走著,车站永远不会到了。我觉得四周,满溢的
已不止是雨水,我好似行走在一条河里。我湿得眼睛都张不开了,做个手势叫李日
替我拿书,一面用手擦著脸,这时候我哭了,我不知道这永恒空虚的时光要何时才
能过去,我就那样一无抗拒的被卷在雨里,我漂浮在一条河上,一条沉静的大河,
我开始无助的浮沉起来,我慌张得很,口中喊著,培,快来救我,快点,我要沉下
去了,培,我要浸死了。
李日在一旁拚命推我,维欣站在一边脸都白了,全身是湿的。“卡帕,怎么喊
起来了,你要吓死我们,快点走吧,你不能再淋了,你没什么吧?”
“李日,我好的,只是雨太大了。”
我跟著他们加快了步子,维欣居然还有一条干的手帕借我擦脸,我们走在公路
,车站马上要看到了,这时候我注视著眼前的雨水,心里想著,下吧,下吧,随便
你下到那一天,你总要过去的,这种日子总有停住的一天,大地要再度绚丽光彩起
来,经过了无尽的雨水之后。我再不要做一个河童了,我不会永远这样沉在河底的
,雨季终将过去。总有一日,我要在一个充满阳光的早晨醒来,那时我要躺在床上
,静静的听听窗坍如洗的鸟声,那是多么安适而又快乐的一种苏醒。到时候,我早
晨起来,对著镜子,我会再度看见阳光驻留在我的脸上,我会一遍遍的告诉自己,
雨季过了,雨季将不再来,我会觉得,在那一日早晨,当我出门的时候,我会穿著
那双清洁干燥的黄球鞋,踏上一条充满日光的大道,那时候,我会说,看这阳光,
雨季将不再来。(注∶柯莱蒂(clytze),希腊神话山泽女神,恋太阳神阿波罗,后变为
向日葵。)这是文章中的初恋.
孤寂的三毛先后真正爱上过三个人,每次都是疯狂地投入。这是她的性格所决定的,做任何事,她都会比一般人付出更多,恋爱也是如此。
上大学时,三毛爱上了戏剧系二年级的一名高材生梁光明大约有三四个月时间,梁光明就像是块磁铁,他走到哪里,就将三毛吸引到哪里。他去上课,三毛就罢了自己的课,跟他去戏剧系旁听。梁光明去小饭馆吃面,三毛也会去,坐在旁边。梁光明上街,三毛也跟在后面。为了接近梁光明,三毛用稿费请客,梁光明虽然喝了三毛的酒,但就是不理三毛。绝望之余,三毛决定主动出击。宴会结束,三毛径直走向梁光明,用笔在他的手心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三毛的初恋从此开始。可这场恋爱仅仅持续了两年,就因两人志趣不同而各自东西。带着破碎的心,三毛独自去了遥远的西班牙。这是生活中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