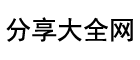史学理论与方法
史学方法论或称历史科学方法论、历史研究方法论。它并不指任何单一的研究方法,而是指关于史学方法的理论,或者说,它是一种可以用于历史研究的普遍方法理论,抑或可以说,拿一定的世界观来观察、分析、解决历史问题便是方法论。在这个意义上,也可称之为“方法学”(methodology)。理论介绍:也正因此,亦因为科学研究中为达到同一目的而使用的方法、手段是多样的,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学派和不同个人那里,史学方法论是存在明显差别的,但它们不见得必定是尖锐对立的,往往是可以相互补充、兼容并蓄的,故史学方法论应是个开放的系统。
历史学理论
史学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
(1)古今中外的任何史学者都有自己的历史观,各不相同。社会历史观是史学本体论的核心问题。概况起来分三类:具有人本主义倾向的史学本体论、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史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本体论。
①具有人本主义倾向的史学本体论的主要观点:第一,强调人的精神、目的、意志是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第二,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无规律可循的。
②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史学本体论。把历史的演进过程归结为社会中的各种结构及其功能的演进过程,认为人的历史命运是被结构决定的。所谓结构就是在一段长时期里总是重复出现的种种“通例”或“常规”。
③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本体论。唯物史观立论的前提既不是历史唯心论者所说的孤立的个人和他们的精神、意志,也不是什么结构,“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所得到的现实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所说的现实前提包括“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唯物史观的原理: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创造出一定的生产力,再加上随着物质生产活动的发展而相应地发展起来的经济交往、社会交往、政治交往和精神交往的实践活动,就创造出相应的经济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和社会交往形式(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形式)、政治交往形式(政治制度和体制)以及精神交往形式(意识形态);这些交往形式逐渐稳定下来,成为世代相传的既定交往条件。“这些不同的条件,起初本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变成了它的桎梏,已成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
(2)史学认识论。史学认识论是关于历史认识、历史认识主体(人、特别是史学家)认识其客体(即客观历史)的过程、特征、方法等等的理论。主要研究人们的历史认识是怎样形成的?人们的历史认识与客观存在的历史之间是什么关系?历史科学的认识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认识有何异同?历史认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阶级性与科学性、相对性与绝对性是什么关系?等等对这些问题的阐述主要包括人本主义倾向、科学主义倾向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认识论。
(3)史学方法论。主要指阐释和揭示历史研究的方式、方法的性质和特别的理论。
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方法论:把历史现象或历史过程分为个别、特殊、一般这样三个层次。①历史主义,包括一是一切社会制度和现象都是历史的产物,进行研究时,应当从产生这些制度和现象的条件出发。二是在分析任何社会问题时,都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三是从发展中考察一切历史现象,从动态的而不是静态角度看待和评价一切历史事物。
②阶级主义,指在承认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级划分出阶级并由此产生阶级斗争的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度……)从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解释社会历史事物的方法论观点和法则。阶级分析基本内容是解开人类文明史一切关系的一把钥匙和进行阶级分析必须研究各阶段赖以生存的各种条件。
几种西方史学方法论简介:①人本主义倾向的史学方法论。其强调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应该是“悟释式”的方法,即要对隐含在有关史料中的历史行为者的意识、意志和行为动机进行设身处地的“移情式领悟”,而绝对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采用法则归纳法对可以观察到的现象的重复性的特征进行数理归纳。领悟而非归纳是他们的方法论的总原则。他们首先运用考证和辨伪的方法对史料进行考察,然后运用“悟释学”方法去领悟隐含在史料中的历史行为者的潜在意识和行为动机。②科学主义倾向的史学方法论。其认为主要研究方法应该是“归纳法”。他们大都倾向于采用跨学科的社会科学方法、比较史学方法和计量史学方法。
(4)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关系
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部分构成了历史科学的理论体系。其中,本体论在史学理论体系中居于前提、核心和主导的地位,因为任何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总是隐或显地以某种史学本体论为其立论的依据或前提的。当然史学本体论的发展论也离不开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的支撑。
历史学理论有助于把零碎的、分散的历史现象联系起来,发现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揭示和认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大的历史问题,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直到社会主义这个社会形态的依次更迭,中间不知道有多少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产生或活动;在前一个社会形态内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往往孕育了后一个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然后便是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和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变革,最后则有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或改革,整个上层建筑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随之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取代了原来的较低级的社会。
小到一个历史人物也是如此,就一个历史人物一生的活动来看,可能是零碎的、分散的,今年有这样的事,明年有那样的事,但是如果能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活动联系起来,理出这个历史人物一生有机的生活脉络,看出这一件件事往往看似偶然其实又带有必然的性质;同时还要和他前代人、当代人做的事情以及后代人做的事情联系起来,才能揭示出他一生活动的规律。
历史理论可以帮助人们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本质。《实践论》“人们对一件事物‘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历史现象只是这个过程的感性认识阶段。理论认识阶段需要在广大的想象基础上,经过科学的形成概念,经过严谨的判断、推理,才能完成,而理性认识阶段就不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他们的外部联系,而是主抓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因为我们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理论的认识。”
史学研究方法有哪些
史学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1、读史证信:阅读史料和分析史料,发现历史的真实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2、孤证不立:为证明某个结论,从不同的角度设计实验或寻找证据证明。3、二重证据法: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以考量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4、跨学科研究:以学科间有关的共同问题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促进学科技术全面协调发展的新学科。还有其他许多方法,感兴趣的可自行了解。
章学诚主要的史学思想和主张是什么
一、历史认识中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一)关于社会历史进步的思想。中国古代史家和思想家对历史发展变化的认识,起始甚早。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把这个问题作为学术争鸣的主要问题之一。自西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形成以后,历代史家自觉探究历史演变的形式及其法则,形成绵延不绝的史学传统。在中国古代史家对历史的认识中,尽管出现过历史倒退观念、历史不变观念、历史循环观念等各种错误认识,然而最有理论价值的则是历史进步观念。章学诚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理论遗产,在关于社会历史演变的认识上表现出明确的历史进步观念。
第一,章学诚客观地考察了人类历史的进程,认为人类社会的形成和演变有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初步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形式及其演变法则。
章学诚论述人类社会的形成,明确指出“人之生也,自有其道。……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②]。这就说明人类社会的产生并不是某些圣人偶然设想出来的,而是按照自身的法则发展变化,是人类生活的需要,揭示出人类社会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章学诚进而探讨人类社会演变的法则,认为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乃是历史的自然发展。他说:“后圣法前圣,非法前圣也,法其道之渐形而渐著者也。”[③]这说明人类社会历史不断发展变化,而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也在不断积累和进步。他对此具体论证说:“周公集羲、轩、尧、舜以来之大成,周公固学于历圣而集之;无历圣之道法,则固无以成其周公也。”[④]阐明了人类社会制度不断发展和进步,有一个不断积累与完善的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章学诚提出的“后圣法前圣,非法前圣也,法其道之渐形而渐著者也”的观点,以前的史家还很少有人能够上升到这样高度的认识。其理论意义在于揭示出这样一条历史法则:社会制度的发展演变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人类不能违背其自然法则行事;后世社会的人们不能单纯效法前人的成规,而应当效法前代社会“道之渐形而渐著”,即效法前人适应历史发展法则而行事的经验,促进社会文明程度不断进步和完善,推动社会历史向更高层次发展。既然社会政治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有其自然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圣人的主观创制,那么如何解释周公创制推动社会进步这种偶然现象呢?章学诚认为,“创制显庸之圣,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独也”,这是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同时又认识到“周公固天纵生知之圣矣,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时会使然也”,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两者相互关系在于,偶然性建筑在必然性基础之上,因而“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而适当积古流传,道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必然性则寓于偶然性之中,所以“自古圣人皆学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阅于自古圣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⑤]章学诚这种认识已经触及历史发展偶然性与必然性相互关系的理论,在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第二,章学诚继承和发展了唐代思想家柳宗元和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等人重“势”的历史观念,更加强调“时势”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深入探讨历史发展的动因。
章学诚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看作是一个自然运动过程,突出强调了“时势”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他批评那些盲目颂扬周公制礼作乐的学者,论证人类社会发展乃“时势”相激的自然运动。他指出:“周公何能作也?鉴于夏、殷,而折衷于时之所宜,盖有不得不然者也。夏、殷之鉴唐、虞,唐、虞之鉴羲、农、黄帝,亦若是也,亦各有其不得不然者也。故曰:道之大源出于天也。”[⑥]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是一个自然的演变过程,并不是后人本质上比前人圣明的结果,而是历史发展趋势造成的。即使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只能顺应历史发展,而不能以主观意志创造历史。他说:“君师分而治教不能合于一,气数之出于天者也。周公集治统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极,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圣人故欲如是,以求异于前人,此道法之出于天者也。”[⑦]章学诚认识到社会政治制度的发展是由“事理”决定的,并不是出于圣人的主观意志。古代杰出人物创法立制,促进了社会的文明程度,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但这并非他们主观上想刻意超过前人,建功立业;而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促使他们必须这样做,是顺应历史的结果。章学诚特别指出上古圣人并非故意求异于人:“天下有公是,成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圣人莫能异也。”[⑧]古代圣贤从事的发明创造,不论是科技成果,还是社会制度、礼仪风俗,都是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产物。既然如此,那么杰出人物的行事也只能顺应客观历史形势。任何社会的杰出人物都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不能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而必须审时度势,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活动。章学诚从这种观念出发,评论孔子的历史作用说:“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创制立法,以前民用。因见《周易》之于道法,美善无可复加,惧其久而失传,故作《彖》、《象》、《文言》诸传,以申其义蕴。所谓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势固有所不可也。”[⑨]说明孔子的事业既适应时代的要求,又受到时代的制约。这种认识是对英雄史观的有力批判,表现出破除迷信盲从,实事求是的态度。章学诚自觉地从“理”和“势”两方面考察社会历史发展趋势及其演变法则,形成了朴素的历史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二)关于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的思想。乾嘉时期的史家中不少人有佞古积癖,在治学过程中逐渐形成矜炫“博古”而昧于“知时”的流弊。章学诚从理论上总结了“博古”与“知时”的辩证关系,在关于古今历史相互区别与联系的论述中包含着深刻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第一,章学诚主张认识历史应当确切把握古今关系,反对主观割裂历史的发展进程,强调史家应当正确认识历史与现实的区别和联系。
章学诚指出,后人在认识历史的时候,既要看到古今历史的相互联系,同时又要注意古今时代的差异。如果把历史和现实绝对割裂开来,就会陷入崇古论之中。必须考虑到古今时代的相互联系,不应在二者之间划定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也不能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这样就会陷入相对论之中。章学诚治史要求明确区分历史与现实,然后分别做出考察,不能混淆二者界限。他非常注意考察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认为不能混淆古今社会的性质:“《书》则言、事杂编,《诗》则风、雅分体,非《六艺》异指也。抒情本性,贵乎因地因时。别而择之,斯为论世。《关雎》说周衰盛,则美刺旨殊;《子衿》言学兴亡,则贞淫义异。贵耳而未尝贱目,以目淆耳则愚;爱古而未尝薄今,以古律今斯舛。”[⑩]他还以古今时代的差异,指出后人行事只要符合时代的事理,就不必拘泥于前人成辙。这就需要摆正古今关系,切忌因“好古”而“律今”,用古代的标准强求现实社会。章学诚在考察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得出了深刻的理论认识:“事有不师于古而因乎理势之自然,有其举而莫之废者,君子之所共由,而不必执古以概今也。”[11]这是说当代社会的某些制度是根据现实形势发展形成的,不一定要从古代社会中寻找理论根据,必须符合古代的制度。
章学诚同时又强调古今社会发展的相因相续,反对人为地割断历史的前后联系。他认为“后之视今,犹今视古也”[12],后人之所以重视古代典章制度,正是由于借古鉴今的需要。这是因为“识今古之典章,……考古即以征今”[13],人们学习历史,就是要通过研究过往时代的历程,认清未来社会的走向。他强调必须重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联系,阐明“今之视昔,亦犹后之视今”[14]的道理,学者治学不能仅仅拘囿于特定时代的学术风气,而应当考察古今历史的发展变化趋势,然后才能得出真知灼见。章学诚深刻地阐述了学者治学通古今之变的必要性:“后世之去唐、虞、三代则更远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15]历史与现实是相互联系的,古今典章制度也具有相通之处,后人之所以要重视和研究古代典制,正是要从它们的继承与发展关系中领会其精神实质,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更好地解决当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章学诚认为“好古”应当学习古人的精神,但却不能处处模仿古人;认识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代社会,而不是为炫耀自己“博古”,也不是要著述流传后世。他指出:“夫师古而得其意,固胜乎泥古而被其毒也。”[16]这种主张是着眼于现实社会,而不是一味地盲从古代,不知变通。章学诚从历史和现实相互联系的角度看问题,主张由古代的礼法制度观照当代社会的典章制度,达到对古今历史的正确认识,这样的见解是相当高明的。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对古今关系具有朴素历史主义的认识。他说:“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17]他讥讽那些只知“好古”而昧于“知时”的人是忘记了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肩负的时代使命:“凡学古而得其貌同心异,皆但知有古,而忘己所处境者也。”[18]旗帜鲜明地表明治学应当着眼于现实时代,而不是仅仅为著作流传后世。由此可以看出,章学诚的认识中闪烁着尊重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的光辉思想,对古今关系问题的认识达到了较高的理论层次。
第二,章学诚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是前后赓续而来,当代社会乃是这个发展过程的顶峰。他关于“礼时为大”的明确主张,是关于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的又一个重要认识。
章学诚认识到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古今时异而理势亦殊也”[19]。社会历史的发展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古今历史发展面貌是不相同的。居今之世,尤其应当注重现实,史家可以“好古”,但不可“泥古”,应该重点关注当代的典章制度,研究历史为现实社会服务。人们认识历史,就是要认识其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从而找到社会历史演变的法则。他认为:“天时人事,今古不可强同,非人智力所能为也。”[20]古今历史发展的不同特点客观存在,并不是人们可以随意改变的。既然古今历史发展形势不同,那么古今社会必然有很大差别。章学诚认为后世必然胜过前代,反对世人盲目崇拜前人和“是古非今”的做法。他强调说:“古今时异,周、孔复生,亦必不尽强今以服古也。……是则先王制礼,有必不可易者,亦有必不能仍者。如井田、封建、宗法,尧、舜不能复行于后世。”[21]章学诚主张根据客观形势制定政策,反对把古人的制度和措施搬用到后世社会,哪怕是古代完美的制度和行之有效的措施,由于时代不同,也不能简单地照搬。他明确指出:“夫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22]这是因为现实的政治制度渊源于古代政治制度,不能割断历史的继承和联系。然而古代典章制度保存在传世的文献中,人们考求古代文献,目的在于更深刻理解当代典制:“制度之经,时王之法,一道同风,不必皆以经名。而礼时为大,既为当代臣民,固当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艺》,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23]章学诚认为现实社会的礼法制度才是人们应当关注的重心,考证历史的终极归宿是要更好地了解和遵循当代典制,而不是要发思古之幽情。他指出:“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鞶帨絺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24]遵时王之制,最终目的还是为现实社会服务。由此可以看出,在章学诚的思想中,注重当代典章制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章学诚关于“礼时为大”的思想,贯穿着厚今但不薄古的社会历史发展观,表现为一种进步的历史主义思想。
二、史学认识中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一)关于护惜“先正苦心”的思想。章学诚从学术有关世道的观念出发,强烈抨击某些史家蔑弃历史,抹杀前人功绩的做法,阐述了后人应当尊重并继承前人的史学成果,不应“轻忽先正苦心”,人为地割断学术文化的发展与联系。
章学诚在治史实践中自觉坚持尊重前人的史学成果,阐明了朴素历史主义的认识原则。他主张“后人述前人,而不废前人之旧也。以为并存于天壤,而是非得失,自听知者之别择,乃其所以为公也”[25]。他郑重申明:“区区可自信者,能驳古人尺寸之非,而不敢并忽其寻丈之善。”[26]后人评价前人既要指出他们的不足,又不可抹杀他们的功绩。他批评清代某些学者“轻议古人,是庸妄之尤,即未必无尺寸之得,而不足偿其寻丈之失也”[27]。但凡心存求胜古人之心的人,虽然攻驳前人不无某些可取之处,但在主要方面却走向谬误,实属得不偿失之举,对于整个学术事业的发展没有促进作用。章学诚指出,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在史学领域中尤为重要。他评价宋代史学说:“夫宋儒之言,岂非末流良药石哉!然药石所以攻脏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见疾在脏腑,遂欲并脏腑而去之。将求性天,乃薄记诵而厌辞章,何以异乎?”[28]宋代义理史学的错误在于矫枉过正,在抨击汉儒烦琐注疏“即器而忘道”的错误方法,强调探究儒学“义理”重要性的同时,把汉代史学中注重征实的合理内核一并抛弃,就像泼洗澡水时连同澡盆中的婴儿也一起倒掉,结果走向了事物发展的反面。针对毛奇龄、戴震等学者对宋明理学的攻击和否定,章学诚认为这是“心术未醇”的忘本行为。他说:“夫空谈性理,孤陋寡闻,一无所知,乃是宋学末流之大弊。然通经服古,由博反约,即是朱子之教。”戴震等人的学术继承朱学而来,“而痛斥朱学,此饮水而忘其源也”[29]。章学诚既肯定戴震等学者矫正宋学失误的成绩,同时也批评他们割裂历代学术联系,全盘抹杀宋人成就的错误,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他们的功过。他主张必须历史主义地对待前人学术:“历象之学,后人必胜前人,势使然也。因后人之密而贬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遗法也。今承朱氏数传之后,所见出于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遗绪,是以后历而贬羲、和也。”[30]章学诚承认历代学术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而这种发展和进步正是建立在前人学术成就基础之上,如果对这种继承关系视而不见,反而轻视前人,显然是不正确的。在今天看来,清代的学术乃是继承宋代学术而来,它不可能跨越这一历史阶段,必然要继承宋代学术的合理内核。清代某些学者标榜自己的学术是直接继承汉代学术,讳言与宋学的关系,违背了历史地看待前人学术的原则,因而是非历史主义的错误认识。章学诚批评历代纂修地方志和家谱的流弊说:“前人纂录,具有苦心,后人袭其书,而不著前人之序例;或仅存序跋,而不著前书之义例如何,则几于饮水而忘源矣。”[31]其实后人修志不重视前代志书,并非前代方志皆无可取,多数情况下是有意掩盖前人成绩,擅自毁坏别人的著作,讳言前人和后人修史之间的继承关系,这是非历史主义的错误做法。章学诚曾经参与修订毕沅主编的《续资治通鉴》,成就远出陈桱、王宗沐、薛应旗、徐乾学诸家同类著作之上。对此,章学诚评价说:“今兹幸值右文盛治,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抄于馆阁者,纵横流览,闻见广于前人,亦藉时会乘便利有以致此。岂可以此轻忽先正苦心,恃其资取稍侈,憪然自喜,以谓道即在是!”[32]章学诚反对“轻忽先正苦心”,没有贬低前人著作的创始之功,而是客观地指出上述诸家著作的成就和不足,并且揭示出造成这种局面的社会原因。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割裂学术之间的传承关系,认识到自己的成绩乃是以前人的成绩为起点,对前人学术补偏救弊的结果,充分肯定了前人的成绩,表现出深刻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二)关于创建史学学术史的思想。章学诚以明确的史学发展意识对历代史学洞察利弊,指陈瑕疵,提出了史学革新的构想,其中主张在纪传体史书里设立《史官传》,全面反映历代史学发展源流,考察其利弊得失,最能够表明他具有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在中国古代史书中,《晋书》卷八二集中记载了两晋的十余位史家,可以视为最早的史家列传;明代李贽著《藏书》,也专门开辟了《史家传》。这表明史家关注史学自身发展的意识不断增强,同时也说明社会对史学作用的认识不断提高。然而《晋书》和《藏书》虽然设立了《史家传》,却是以叙述史家生平事迹为主,仍然属于人物传记的范畴。从这样的史家传记里,看不到史学发展演变的轨迹和趋势,更难以考察某一时期史学利弊得失的总体面貌。
章学诚认为应当改变过去史书为史家立人物传的做法,主张集中设立《史官传》。他明确指出:“列传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33]章学诚进一步阐明了设立《史官传》的重要性。他说:“夫作史而不论前史之是非得失,何由见其折中考定之所从?昔荀卿非十二子,庄周辨关尹、老聃、墨翟、慎到之流,诸子一家之书,犹皆低昂参互,衷其所以立言;况史裁囊括一世,前人成辙,岂可忽而置之!”[34]他强调设立此传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总结某一时代的史学成果,让后人继承和发扬史学家法。章学诚认为,司马迁、班固等人是具有这种史学意识的史家,可惜这一传统随后中断。他说:“史家著作成书,必取前人撰述汇而列之,所以辨家学之渊源,明折衷之有自也。……况史学之重,远绍《春秋》,而后史不立专篇,乃令专门著述之业湮而莫考,岂非史家弗思之甚耶![35]其结果造成人为地割断史学发展的前后学术联系,倘若恢复这一优良传统,专门设立《史家传》,就能最大限度地继承前人的学术成果。二是通过记载历代史家及其学术流派,使后人能够认识前代史学中的利弊得失,借鉴经验,吸取教训,评价其是非功过。章学诚列举范晔撰《后汉书》,隐括刘珍、袁宏、华峤、谢承、司马彪诸家后汉史书而成;唐初撰修《晋书》,整齐王隐、虞预、何法盛、干宝、臧荣绪等18家故事成书。但是,《后汉书》和《晋书》都没有条别诸家史书体裁义例,论次群书得失。史家修史对前代史书内容“不为叙述讨论,萃合一篇之内,何以得其折衷?此诸家流别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36]。尤其是唐宋以后史馆集众修史,更应该说明具体分工情况,标明某纪、某志编自何人,某表、某传出自谁手。只有这样,后人才能考察史书质量臧否,评论史家史识高下。如果“不为整齐缀合,各溯所由,未免一书之中优劣互见,而功过难知。此一书功力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37]其实这并不困难,因为后代史家为前代史家作传时,必然能够看到他们的著述材料,明晰史实原委,足资考证;若把这些内容集为一编,或为一人单独立传,或为诸家集体立传,便于后人考察其学术全貌。章学诚认为:“后人修史,不能条别诸家体裁,论次群书得失,萃合一篇之中,比如郢人善斫,质丧何求?夏礼能言,无征不信者也。他若聚众修书,立监置纪,尤当考定篇章,覆审文字,某纪、某书编之谁氏,某表、某传撰自何人,乃使读者察其臧慝,定其是非,庶几泾渭虽淆,淄渑可辨。”[38]这些事迹若不及时编录,很快就会散失殆尽。由此看来,前史虽有《史家传》,不免荒略太甚,无法适应史学发展的需要。
章学诚提出仿照学者记述经学师承的《学案》义例作《史官传》,改变过去写人物传的做法,以史家著述为经,传承流别为纬。例如后人作《司马迁传》,首先要叙述他撰《史记》时参考了《尚书》、《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然后再叙述《史记》撰写的经过,最后叙述杨恽传布其书,徐广、裴骃等人为之作解。又如后人作《班固传》,首先要叙述他参考了司马迁、扬雄、刘歆、班彪等人的著作,再叙述撰《汉书》的过程,班昭、马续等人补作情况,最后叙述服虔、应劭等人为之作注。“凡若此者,并可依类为编,申明家学,以书为主,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则《春秋》经世,虽谓至今存焉可也。”[39]倘若某个史家事迹较多,地位非常重要,则应在《史官传》内载录姓名,著明此人另有专传。章学诚在阐述了《史官传》的具体做法之后,又着重总结了设立《史官传》在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他说:“马、班作史,家法既失,后代史官之事,纵或不能协其义例,何不可就当时纂述大凡,人文上下,论次为传,以集一史之成乎!夫《儒林》治经,而《文苑》谈艺,《史官》之业,介乎其间,亦编摩之不可不知所务者也。”[40]强调史家所从事的事业极为神圣,应当独立于经学、文学之外,成为一门体系完整的专门学科,真正实现自司马迁以来史学自成一家的目标。由此可见,章学诚设想的《史官传》有利于全面反映史学学术思想发展,清晰地显现出史学发展演变的源流。从《晋书》为史家集体立传,仅叙史家生平事迹;到章学诚主张《史官传》叙述史家作史的学术源流与得失,不仅标志着史家对史学自身认识的提高,而且反映出朴素历史主义思想的不断发展与深化,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史学批评中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中国古代史学中曾经出现过各种非历史主义的史学批评方法,不同程度地造成了史学批评的失实。章学诚借鉴了前代史家在史学批评方法上的经验和教训,对史学批评方法论做了深入探讨,形成了朴素历史主义史学批评思想。
章学诚是如何论述史德的?
仔细研读《文史通义·史德》全文后,可大致梳理出章学诚先生的行文脉络和论述史德的逻辑。首先,《史德》中观点的提出,是章学诚以为他异于刘知几的地方,所以在文章开始,章学诚就先论证了“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他认为刘知几所谓史识只是“文士之识,非史识也”。那真正的史识应该是怎么样的呢?章学诚在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接下来就是要说明什么是史德了。“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章学诚为史德下的定义是史家的心术。心术二字是《史德》全文的中心。然后,章学诚先生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一、为何要辨心术以议史德,为什么说“心术不可不虑”“心术不可不慎”。二、如何养心术。在阐明第一个问题前,章学诚先生先提出了一个良史的标准:“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以此为标准,史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心术”呢?章先生继续说:“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可见,心术与“天”“人”密切相关。那么“心术不可不虑”的原因就在于“天与人参,其端甚微”。章先生解释道:“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盖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焉。”史传作家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是由历史事实所体现的,而史学的外在形式史书,却还要依赖于史家的劳动。在活生生的历史事实面前,史传作家往往“因事生感”,使情与气默运潜移,“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积而情深本是文章之上品,但史文之中,既有客观史实,也有史传作家的主观思想,所以“有天有人,不可不辨”。那么如何辩天人之际呢?既然史家是由于气情牵动心的变化而导致天人之别,那么就应该由气情来辩天人“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文总要借助人力以成,人因为气情的变化却有“阴阳之患”。“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毗于阳矣”,“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毗于阴矣。”而“阴阳伏沴之患,乘于血气而入于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所以历史书写中“益于人”通常连史家自己都没有察觉到,欲作良史,真是“心术不可不慎”啊! 接着,很自然地就过渡到了第二个问题。气情的变化使人具阴阳之患而不能做到“尽其天而不益与人”,那么养心术就要养气情了。章学诚先生提出要“气平情正”。那怎么样的人才能“气平情正”呢?韩氏愈曰:“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仁者情之普,义者气之遂也。所以养心术就要通六艺比兴之旨,也就是“心术贵于养”,应明纲常名教之理。接着章先生以司马迁为例,说明此理。“《离骚》不甚怨君,后人附会有过”“ 史迁未敢谤主,读者之心自不平耳”,可见“好善恶恶之心,惧其似之而非,故贵平日有所养也。” 这样,章先生就围绕“心术”这个中心,以“气情”为基础,以“用名教养气情”为修炼之法,达到“尽其天不益与人”的良史标准,从而完成“史德”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