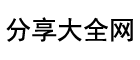智库是怎样炼成的
智库是怎样炼成的
2001年,Marshall Bouton担任了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的主席。这是一家研究对外政策的智库,但却不在首都华盛顿。Bouton任职的时候,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已经逐渐被边缘化。他们有一个传统项目,每两年一次的关于全球政策的民意调查,但关注的人也越来越少了。Bouton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打一场翻身仗。他不想撤退,而是想要出击。他要让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不再成为一个地区性的智库,而是全国性的智库。这就需要大胆而缜密的规划。Bouton的策略是选择那些既和地区利益有关,又有全国影响力的研究题目:比如食品政策,因为芝加哥是美国中部的粮仓;又比如穆斯林移民政策,在芝加哥所处的美国中西部地区,穆斯林移民的比例急剧攀升。重新定位之后,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很快就如枯木逢春,在五年之内,他们的经费从480万美元提高到了730万美元,会员增加了49%,参加他们的年会的嘉宾人数增长了50%。
智库也需要战略。对于一个智库而言,首要的任务是确定自己的定位。你要么找到一个别人没有发现的领域,要么找到一个别人没有发现的角度。正如蓝海战略的提出者金伟灿(W. Chan Kim)和勒妮·莫博涅(Renée Mauborgne)所说的那样,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最好办法就是避开竞争。智库和企业一样,也要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Niche)。各种智库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兰德研究所依靠军方的雄厚支持,可以潜心于深入的技术性研究。传统基金会明确地自我标榜是一家“保守主义”的智库,引来了无数铁杆支持者。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简称MPI)坚持“把一壶水烧开”,只专注于和移民有关的政策研究。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不满足于只做美国的智库,他们要在全球建立自己的影响力,担当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互相沟通的桥梁。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更是特立独行,他们做的是民意调查,只摆事实,不讲道理,他们自称是“事实库”(fact tank)。曾经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鲍尔森卸职之后,自己搞了个研究对外投资的智库,他的志向是建“Do tank”。
智库被称为“思想的掮客”,主要的宗旨是为了影响决策。做研究的人很多,但大部分是在高校里。高校的研究是为了把科学前沿进一步向前推进,智库的研究是跟在后面捡麦穗的。做智库研究,不需要太高的智商,但需要多面手。要会做研究,知道怎么用理论和数据得出可信的分析,还要能把复杂的思想用简明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既要讲得领导听得懂,也能讲得普通百姓听得懂。不仅要弄明白是啥,还要弄明白该怎么办,有什么高招。不仅要把“一方面”、“另一方面”都摆出来,还要敢于在不同的情景中做出判断:禽流感会不会大规模爆发?欧洲债务危机会不会传导到中国?油价会涨还是会跌?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有不少学者能做高深的学问,就是写不了政策报告,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知识的诅咒”:他知道得太多了,不知道该突出哪些要点、忽略哪些细节。官员用的语言和学者用的语言不是一个体系,有经验的政策研究者得学会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中跳进跳出。
对于智库来说,想要影响政策决策,大体是在议题的提出、寻找不同的政策方案、推动提案的通过这三个阶段。研究型的智库大多会集中关注第一个阶段。比如在朝鲜战争的时候,兰德智库只告诉美国政府,中国会出兵朝鲜,至于怎么决策,那是政府自己的事情。大多数智库还会服务到第二个阶段,即要拿出不同的政策方案,供决策者选择。有个别和政府关系格外紧密的智库会热衷于在第三个阶段发挥作用。比如在小布什总统期间,当美国成立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简称 DHS)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个新部门该干啥。传统基金会马上行动起来,写报告、开研讨会、四处游说,对国土安全部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仅仅是亦步亦趋地跟在政府屁股后面的智库是不可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的。很多长期问题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准备,更不可能给智库布置具体的研究任务。一流的智库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前瞻性的问题,事先准备好政策建议,早早地赶到前面,搬个小板凳,在政府要路过的地方等着。布鲁金斯基金会讲到,他们的学者大概会用60%的时间做长期的战略研究, 40%的时间做应急课题。这样做还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谁也不知道未来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所以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研究一定会有失败的可能。这是一种“对智力的风险投资”。有活力的智库,都会对失败的研究抱有更多的宽容。
智库不仅要面向政府,还要影响公众。智库和高校不一样,并不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为考核标准,它们鼓励自己的研究人员在报纸上当撰稿人、上电视、参加各种公共论坛,发出自己的声音。布鲁金斯基金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等智库都鼓励自己的学者写书,不是那种晦涩难懂的学术专著,而是能用平实的语言把一项政策的来龙去脉讲得头头是道的通俗读物。在互联网时代,智库们也学会了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推广自己的观点。和传统媒体相比,社交媒体的成本更低、传播面更广,而且能够形成互动。当然,互联网也会极大地降低每个人发表意见的门槛,这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能够把自己的观点和网民的吐槽区分开的,最终是靠智库的信誉,这种信誉归根到底来自于扎扎实实的研究。
一般来说,智库的规模都不大。当然也有非常大的,比如布鲁金斯基金会每年的预算大约在8000万美元以上。有的智库规模小的令人吃惊。地处布鲁塞尔的Bruegel,这两年异军突出,超过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跃居全球经济政策类智库第一名。Bruegel的研究人员不过10人,其中还有兼职的。大多数规模较小的智库,都得学会灵活地运用访问学者、客座研究员等机制,把自己建成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智库的竞争力不在于单独一个、两个一流的学者,而是一个充满战斗力的团队。小而精干的智库之所以有竞争力,还因为他们像培养科研骨干一样培养行政和后勤人员,有一套标准化、流程化的工作方案,有各种各样的科研管理创新。这些科研人员背后的无名英雄,很多都是藏龙卧虎。Bruegel的媒体联系负责人原来曾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战地记者。
比做研究更令人头疼的事情是筹资。智库的资金来源,一是靠基金会的支持,二是靠大大小小的捐款,当然也有课题经费和公司、个人的馈赠。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智库更容易收取捐款,比如传统基金会、卡托研究所主要依靠捐款。他们的捐款人数众多,就跟收党费一样。相对保持政治中立的智库则主要靠基金会和课题的支持。为什么筹资难,不是难在要钱,而是难在说服更多的人,你的事业也是他们的事业,你要做的事情也是他们想做的事情。募捐不是仅仅筹集资金,而是汇集志同道合的力量。一个优秀的智库,一定是有灵魂、有感召力的。离开了这种灵魂,智库也就没有了生气。
所以说,智库的战略不是学得来的,智库的战略镌刻在它的DNA里,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体现着它的战略。
【作者注】本文取材于Andrew Selee,What Should Think Tanks Do? A Strategic Guide to Policy Impac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作者是威尔逊中心墨西哥研究所的高级顾问。他这本书主要采访的是美国的智库,较少涉及其它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智库。中国的智库建设和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异,本文的介绍仅供参考和批评。
全球顶尖的著名智库有哪些?
《全球智库发展报告2013》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TTCSP)”的研究成果,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是其在中国唯一授权单位,这也是报告中文版在我国首次正式发布。 报告显示,2013年,全球智库数量为6826家,比2012年的6603家有所增加。其中,北美洲最多,共有1984家,欧洲有1818家,而亚洲排第三,有1201家;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有1828家,是第二名中国425家的4倍多,第三名英国智库287家。 2013年度全球智库第一名仍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目前,美国仍居国际智库首位,影响力居前列。布鲁金斯、卡内基、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美国外交委员会、美国兰德公司等连续多年居国际排行前列。印度等金砖国家智库数量也在不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