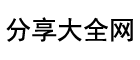因疫情冲击而推迟结婚或怀孕的现象在日本变得普遍,日经中文网报道称,“2021年的出生人数可能低于80万”。常年苦恼于少子老龄化的日本政府最近又开始“整活”了。
上周五,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消息,日本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到2031财年,国家公务员的退休年龄将从目前的60岁分阶段提高到65岁。从2023财年开始,日本国家公务员普通职员的退休年龄每两年延迟一岁,原则上年满60岁就要离开管理岗,且薪水减至原来的七成。
去年2月内阁通过的另一项法案则敦促企业允许员工工作到70岁。日本经济新闻社最近公开了从2019年开始的一项调查结果,其中表示愿意工作到70岁以上的60~69岁受访者占比54%,同比增长了9%。
“打工吧,老年人”“如果70岁还要工作,那真是‘为了老板出生,为了老板而死’。”将满而立之年的林裕亮对这样的未来十分抗拒,认为赞成70岁继续工作的人是对自己的生活有危机感。日经的调查印证了裕亮的猜测:年收入在3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18.9万元)以下,以及收入不稳定的群体更倾向于继续工作,同时有高达76%的受访者对自己晚年的健康和经济状况感到不安。
23岁,刚从大学毕业进入职场的安藤诗织却坦然接受:“我们没得选。”诗织家的长辈中不乏退休后夫妇二人继续兼职工作的,他们满足于自己还能为社会提供生产力。日经的调查也显示,越接近退休年龄的人对70岁后继续工作的接受度更高。尽管就业不满一年,诗织也有了规划晚年的意识,“因为我们会活非常长。你看我爷爷,都已经九十岁了,还能整天自己开车出门,尽管我们都劝他不要做这么危险的事。
当地时间2019年9月16日,日本东京,一名老年安保人员在当地购物街清理街面 / IC Photo
作为世界上老龄化最快的国家,截至2020年9月的政府统计显示,日本65岁及以上人群占据总人口比重高达28.7%,中位年龄为48岁,到2036年这一比重还会提高到三分之一。比诗织爷爷更年长的百岁老人大有人在,且有足足八万余人之多,刷新历史记录。
与此同时,日本自1974年以来一直未能将生育率提高到2.1的替代水平。自2011年以来,日本的人口一直在不断萎缩。2018年平均每名日本妇女生育1.42个孩子,而欧盟同期的数字为1.55。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在2017年预计,如果以中等生育率推算,2065年日本的人口将降至8800万,而如果按低生育率的情况,则会降至8200万。
“一个适合老人生活的社会,年轻人要过得好是不太容易的,”提到养老金,裕亮和诗织的反应都是瞬间放声大笑,直言自己从没指望过靠养老金(国民年金)度日。裕亮理想中的情况是拿到17万日元一个月的国民年金,加上自己的存款和其他补贴才足够晚年花销。
放弃“鸡娃”,但两个是极限从现在开始提前储备“老后生活”的同时,裕亮还需要把育儿开支考虑在内,“我想有一两个小孩,是男是女都可以。我是独子,如果没有小孩我们家就会‘灭亡’。”裕亮发现和自己家一样的华侨家庭鲜少有人不在意传宗接代,相比之下非移民家庭出身的同辈好友对于“不生育”这个人生选项的宽容度更高。“如果我35岁前能达到平均收入的话,一两个孩子还养得起的。”日本厚生省公布的2019年平均年薪为458万日元(按最新汇率计算约合人民币26.8万)。
不同学校系统教育费用比对 / 网页截图
裕亮一家生活在濒临濑户内海的日本第七大城市神户,父母分别是体育老师和幼教,裕亮从小读私立的中华小学,而到了他这一代更倾向于把孩子送进公立学校:如果从小学到大学都是上公立学校,学费开支是日元731万左右(约人民币42.7万元);从小报兴趣班的花销也可以“丰俭由人”,一个月最基本的钢琴课2-3万日元,游泳课1万五千日元。“我上个月给几个公立学校的孩子做家教,我看他们没什么学习压力,除了兴趣班之外很少从小学开始上学业补习班,而我只希望孩子达到普通水平就可以。”从私立初中开始一路准备到能上东京大学做医生那种精英路线并不存在于他的世界之中。
从2012年后修改的儿童津贴政策按家庭收入水平差异向每个小孩每月发放最多一万(3-15岁)和一万五日元(0-3岁)的补贴。“一万日元顶多够给孩子多报一门兴趣班,”裕亮调侃道。
自民党在去年11月还主张把一次性生育补贴从42万日元提高到大约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9万元),针对的仅是生孩子时的花费。
普通人对这项政策的反应同样冷淡。“这只是加总全国各地方的平均水平,在东京的话,补贴的数字起码要翻一倍才够吧。”和现任首相菅义伟一样来自秋田县的诗织并不介意结婚后搬到另一半的老家生活,随着远程办公的工作形式成为常态,离开东京反而可以节约养育成本。
日本时报称,2020年4月至10月期间东京的报告怀孕数量仅有6万例,与前一年同期相比下降了约10%。今年一月,因为在东京生孩子的平均医院费用比其他地区高出10万日元,东京的一项新提案提出给每个新生儿奖励10万日元的信贷,用来兑换儿童保育服务,计划还没通过和推行就招致舆论反扑——毕竟,10万日元在全部养育成本面前简直是杯水车薪。
“职场妈妈困境”“我这30年里,从来没见过日本经济好的时候。物价越来越高,工资水平倒是没有变过,”裕亮认为,有人口焦虑是发达国家的正常现象,但经济增长迟滞带来的生活压力是年轻人难以扭转的处境。
对于诗织的母亲而言,成为母亲是她的梦想,做家庭主妇也是同龄人的普遍选择,但到了诗织和裕亮这一代,夫妻二人都领工资才能更好地支撑家庭的经济状况。裕亮告诉世界说,“除非我能达到上千万日元的年收入,否则按450万日元的一般年薪,最多只能支持妻子辞职在家育儿两到三年。家庭经济是是需要女人回归职场的,但整个社会对于有孩子的女性来说,很难兼顾工作。
2018年日本千叶市的一场大学生招聘会,在日本,女性职业生涯常常在婚育后中断
商科毕业的诗织在一家人工智能领域的初创公司做客户服务兼销售的工作,朝九晚六,加班到7点是常态,相当于每天工作超过9小时。“我进入这家公司是为了让机器和AI减轻人类工作的负担,结果我自己却每天在加班,”诗织笑称自己处于压力很大的上升期,每天都需要往脑子里塞各种新的知识,但如果几年后成为母亲,会换一份不用加班或者可以远程办公的工作,一是想提供更多陪伴,另一方面因为女性薪水相对低,只能作为家庭经济来源中锦上添花的一部分,承担更多照料小孩的责任。
2018年日本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的性别收入差距第二大的国家(24.5%),第一名是韩国。同时,当女性很常见地退出职场照顾孩子时,职业中断也会导致未来到手的养老金金额的差距。
另外,托育服务的不足加剧了在职母亲的负担。早在2001年保育所无法满足大量儿童入学需求的问题就持续浮现。保育所隶属厚生劳动省,负责帮助因工作繁忙的父母照顾出生后57日到入学前的儿童,一天8小时,部分还接受12小时托育。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18年4月全国等候入学名单上的儿童人数四年来首次下降,低于2万人。而东京是最难申请入学的地区,等待名单上“待机儿童”数量最多,直到2018年才第一次下降到只有5414人。由于薪资水平低(工作年限8年的女性保育士年均工资21.3万日元,男性23.1万日元,约合月薪一万人民币),休假少,休假难,工作责任大压力大等原因,保育所人手不足导致招生人数有限,在职妈妈没法把小孩送到保育所再抽身去工作,甚至连兼职工作也难兼顾。
今年4月1日,菅义伟称拟建立“儿童厅”以改变内阁府,厚生劳动省和文科省在育儿支持政策中各执一端,导致补贴申请程序繁复,施政效果管理难等问题。虽然看得到政府的决心和政策背后的焦虑,裕亮仍然忍不住吐槽,“绝对没用,为什么我说绝对呢?你看看想出这些办法的政客,他们这个年纪的人肯定没带过一天小孩,都是扔给太太去带的。”
诗织住在以高级住宅闻名的大田区,每当诗织看到独自推着婴儿车带娃走在街上的女人,总能对她们的辛苦感同身受。“我经常能在街上看见男人和他们的狗,却几乎没见过男人带着他们的小孩,”诗织从小和父亲相处的时间也很少,父亲作为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每天从早上六点工作到晚上11点,只有在周末或者假期能陪伴家人,和两个女儿在院子里堆雪人。“我很感激爸爸这么辛苦工作才能供我上大学,”诗织说,“但是如今和我同龄的女性对男性在家庭中的角色有了新的标准——必须承担家务。
2021年日本性别差距报告(经济,政治参与,教育和健康四个维度)与全球平均水平对比
另一处让诗织略感烦恼的是,她在结婚后就必须随夫姓。“我很喜欢我家的姓——‘安藤’。一想到结婚就要改姓,我很不高兴,很讨厌日本这一点,甚至觉得搬到挪威或芬兰也不错。”诗织说她的好友Katasato就宣称为了保留自己的罕见的姓氏而决定不婚。
在世界经济论坛于2021年3月31日公布的最新《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日本在156个国家中排名第120位。虽然它比2019年12月上一次报告时的第121位上升了一位,但仍处于垫底群体,且日本妇女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参与度仍然很低。诗织告诉世界说,“虽然我不喜欢政府继续办东京奥运会的决定,但奥运也成为了媒体和舆论的一个契机,希望政府能作出改变,让社会变得更加平等和正义,这才符合奥运会的价值。”(责编 / 张希蓓)